文革结束之后,整个国家和我个人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我个人在这个时期已经没有机会实现我上清华做理工男的梦想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因为还在工作状态没有赶上,后来我的年纪很大,31了,没有读大学就考了一个研究生。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参与了一些党在转折时期的工作。1977年1月份,我还没有读研究生的时候,在中央宣传口工作,当时我们党的中央宣传部已经取消了,所以中央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临时建立了部门一个叫做“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是耿飚,地点在钓鱼台。
当时党内发生了“两个凡是”和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整个从中央到各个地区的高级干部都卷入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都要照办,毛主席决定的都要具体执行”,这个实际上是坚持过去老的错误的认识。后来由小平同志推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就把我们整个党的认识路线拨回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我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另外我在那个时候也为我父亲起草了一些发言提纲。当时我父亲从监狱里出来逐步恢复名誉、平反,后来成为当时十一大的中央委员,参与了中央的一些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起点,我们现在确定改的革开放元年是在1978年12月22日,就是以这份公报作为起始的。我后来有机会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因为我学的经济学。但当时副总理级的国务委员张劲夫,让我做他的秘书,他认为我作为年轻人能够帮助他和各方面联络。他101岁去世的,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推动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在这段期间我也对政治生活的进展做了一些工作,包括清理“三种人”等等。1984年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人生的节点,当时我对一些政治上的文革的事情曾经上书给陈云同志,得到了陈云同志的肯定。1984年6月,我第一次出国。今天出国对于在座的各位不算新鲜,用各种方式,旅游、访学,还有暑期的活动等等,但那是我第一次出国,那一年我37岁。当时一下去了六个国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眼花缭乱,很快,回来以后又去了一趟日本,我对去日本那边看到的感觉,他们富裕跟我们的鲜明对比,使我受到很大的刺激。
我们去坐新干线,现在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跟我们的高铁比是小菜,但当时我们坐新干线时的震撼难以形容。张劲夫是老同志,他跟我说:“日本哪里来这么多的水泥,这么多的钢铁?怎么有这样的技术,怎么有这样速度的交通?”我们觉得我们差距太大了,他说作为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一定要推动改革开放,所以我说他们为什么有那么急切的心情要学习,要开放,和这个感受是有直接关系的。

代表团成员在塞纳河上
1984年发生了很多事,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莫干山会议,如果你是学管理和经济学的,对中国改革史有一定的了解,一定知道莫干山会议,我不久前刚从那儿回来,今年是莫干山会议35周年。35年前,一批30多岁的学者、青年经济工作者,在浙江德清县开了一个会,会上124个人分成七个组,对农村改革、价格改革、对外开放、计划经济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等等彻夜地争论,提出了很多意见。
当时开会的人物都有谁呢?有前面提到的王岐山、马凯,还有朱家明、彭家南等等一批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提出当时在中国继续推动关键性的价格改革,因为中国计划经济原来的价格体制,是小小的一盒火柴,价格变动哪怕一分钱都要测算,这对全国人民的消费负担带来多大的影响,何况那些轻工业品、那些农产品都是非常严格的。
中央正在酝酿价格改革,用什么方式改?有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会上有主张一步到位的激进派的意见,还有提出来的渐进式,所以最后提出来双轨制。我知道要开会,就拉着当时的总理秘书,也是我们的同学上山跟他们沟通,他们晚上去,早上回来,选了一批他们的研究成果。然后经过选择选了七八个学者下山,张劲夫同志亲自跟他们座谈。最后劲夫同志经过整理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总理,说他们的意见很值得参考。然后当时的总理也批了,说很开脑筋。这样就把这个意见吸收到当时国家推动的价格改革中去了。
其实双轨制改革是有利有弊的,大家对经济学有一点概念吧,比如说我这个同样的产品,它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计划价格假如说是五块钱,如果市场价格是八块钱,那会形成什么呢?寻租,拿到五块钱的指标了,无论是钢材,无论是水泥建材,无论是外汇,比如说一美元两块八人民币,但是实际上在市面上六块、七块、八块,所以缺点是明显的,以至于后来在价格闯关中间形成了一个反复。

“莫干山会议”参会者合影
但是这体现出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中国推进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而没有走美国经济学家给苏联设计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式的变动。渐进式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似的改革,大家知道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元年,但是实际上那时候没有真正的顶层设计,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蓝图。所以这个改革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我想跟大家说,我作为那个过程的参与者,从实事求是、思想解放、反对两个凡是等等,一直到具体的操作探索改革的具体方案,我是有幸参与了。
再说回我个人,我本来可能按照常规会去从政,就是现在说做公务员了,到政府里面去了,但是我自己思考,我觉得我可以做点尝试,所以我就到第一线,到市场里面去了。这样就形成了我的一个转变,在光大和中信。
我在2010年的年底要退出现职工作了,当时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跟我谈话,对我工作有评价,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了这句话,“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工作多少年,工作卓有成效。”我很惭愧,我觉得这是中央组织对我的一个肯定,但是实际上我自己做的是很不够的。我简单说一说光大是一个什么样的产物。中信1979年就建立了,光大是在它之后四年1983年建立的,我先到了光大。
光大把总部设在香港,这是一个非常睿智的安排,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开始推行引进外资。其中对于外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三减两免”所得税——三年减半,两年免费,香港的港资当时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平台,对它们也是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所以光大总部设在香港。

光大集团1990年迎春酒会合影
但是在探索中间也会发生问题,因为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有一些东西我们并没有掌握规律,而是盲目地照抄照搬,所以当时光大下面一个公司,外汇交易一共亏损了四千万美元,又加码投入资金再做,这样最后亏损了八千万美元。又因为光大信投采用了高息揽存,吸收了一百几十亿的资金,我们高额成本投资出去以后没有真正的回收,形成了巨大的负债,当时我受命去处理这些问题。
当时的问题非常严重,一直到了由国务院亲自处理,我们的方案向北戴河李鹏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办公会议汇报,确定了一个债转股的方案。这个过程因为时间原因不多讲了,就是在探索中出现的问题,我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机缘,就是我自己经常受命处理和化解危机。
我接下来讲中信,中信是值得一说的,我在中信待了十年。中信的起点是1979年的1月17号,小平同志请了荣毅仁还有其他几位老的工商业者座谈,在大会堂,叫做五老火锅宴——非常亲切、非常和谐的这样一个气氛。目的很清楚,就是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听一点你们的看法。
他们一边吃涮羊肉,一边就谈出来很重要的思想。怎么来试验?从点到面来找出经验。然后小平同志直接提出来,组织一个公司,你来尝试,你来探索,人由你来选,事你定。
这个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安排,我最近研究中信的历史,我们怎么形成今天这样一个产融协同发展的格局,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改革开放没有一个总蓝图,没有一个顶层设计,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探索的过程就需要有抓手,现在大家都知道最具有效力的抓手是特区,深圳就是起到示范效应和现代的改革开放支点作用的特区。

中信的起点:“五老火锅宴”
还有一个抓手是两大窗口公司,它的探索机制要比它取得经济上的成效更加重要。
当时国家的整体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里的企业都是国企,没有真正的所谓私企、民营企业。所以要跟国际交往,需要用一些特殊的办法,所以就成立了这两个公司,什么叫窗口公司,我觉得这是小平同志做事情的战略眼光,同时又是很实实在在的工作方式——就是抓试点,抓重点。所以我们在发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同时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投投资公司。而且外资经营企业法是征求了荣毅仁同志的意见,因为他比较熟悉外商的工商业界,当时提出给外资一定的股比才能有这样的作用。
开始中信的使命叫做“三引进”——引进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引进管理经验,另外它还是一个创举,中国国际信投投资公司,本身既包括金融,也包括了实业——你看他叫“信托”体现了金融,叫“投资”就是体现了实业,因为荣毅仁同志一直笃信实业救国,大家知道荣氏家族在上海纺织、面粉等实业方面方面有非常厚重的基础。同时公司的名称中还有国际两个字,就是开放。所以我们中信的标志也是荣老板亲自设计的,这是经典之作。我觉得确实有些人他们有特殊的能力,把握了这个历史的关头做了这个特殊的工作。
中信创立之初注册资金两个亿,但是拨了一个亿还没有到账。当时就要组建了,荣老板拿了一千万给公司作为启动资金。我们的开拓创新成就了一系列的首创,首创不容易,首创不一定特别的成功,但是首创具有探索的意义。所以我们第一家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第一个直接进行海外投资,还有我们涉及到通用卫星、境外放债等等。
中信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我们的金融曾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中信银行跟所有的大行在2002年都遇到了严重的不良资产,当时海外的投资银行界认为中国的银行业是整体处于技术性破产的状态,就是资不抵债。由于不良资产太多,如果按照实实在在的会计准则拨备核销的话,我们净资产会被吃光,当时我们的累计不良资产大约在三百亿,我们全行业资本金不够六十多亿。这三百亿不良资产按照会计准则要拨备和核销,一共要核销二百亿,核销完之后变成负资产。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时整个中国的银行业在九十年代末期成立了四个资产管理公司,从中信剥离了一亿四千万的不良资产。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到国务院申请了批准发债,然后补充了资本金。
2007年我们在两地同时上市了,叫做自费改革,我们中信人引以为自豪的是几乎所有的银行都伸手从国家拿到了资金的支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它们不但剥离资产,而且在2002年、2003年又再次剥离,剥离之后还不行,还要大量注入,一个银行注入两百多万的资本金来解决它们的整改和上市。而我们完全靠自己,我们叫做自费改革。另外我们在香港上市,建了一个很好的试验窗口,这是我们中信人引以为豪的,曾经因为资不抵债被看成三钱不值两钱,我当时提出来“背水一战”,要“卧薪尝胆”,我们一定要把三钱变成十钱,后来我们在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市盈率到了39倍,我们的市净率到了三倍,认购率到了90,最后融到的资金是接近60亿美元,所以我们打了一个胜仗,成为我们中信的一个历史发展节点。

2007年,中信银行在上海、香港同步上市
这个是我亲自参与的,2017年我们上市了,们当年整个中信集团的盈利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一百亿,达到了160亿的净利润,2006年是60亿,上市之后是160亿,我们正在发展的一个胜利的期间,又来了问题。银行上市本身是一次危机处理,然后我们又遇到了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叫做中信泰富,它为了做澳洲的铁矿项目做衍生产品,亏损了154亿港元。
当时9月15号金融危机在美国发生,我9月21号到纽约,正在感受他们的压力和危机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说咱们也出事了,我电话里就问是几位数出了事,回答说是两位,我又问,两位数会不会往三位数走?对方说正在往三位数走,巨额的亏损。那时候我正跟美国人有点调侃地说,你看我们比以前强大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承担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所以我们比你们还是不行。话音刚落,我们自己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来了,最后整个亏损154亿港元。
这对我个人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是中信的董事,我们在中信占比30%,荣智健他们是20%,我们有一种方式就是壮士断腕,断腕不够,会发生信用方面的连锁反应和履约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形成交叉违约。最后我们派了两个调查组——一个是财务,一个是业务——到香港做了调研以后,我们就开了一天的闭门会议,最后决定用一种方式来拯救。
这个方案现在大概凡是投行的人都认为是特别经典的成功案例,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当时我们把所有的合约按照一个澳元换0.7美元定价,由中信集团接过来。大家注意它还不是一个上市公司,它有大量的小股东受损,所以我们接过来等于把损失在某一个时间点锁定了。每一分钱,0.69我们赔两亿港元,如果变成0.6,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多赔20亿港币,当时我们说要研究,能不能不要掉到整个集团净利润一百亿以上,因为我们员工头一年超过一百亿以后心气很足,心理关头能不能堵住。
第二个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们怎么做呢?每股八港元注入,市场价格是四港元,市场价格就是股东手里抓的钱。八港元需要小股东投标,我们比他多一倍,小股东99%赞成,因为觉得我们大股东宁肯牺牲自己也要维护企业的股东利益。但是其实每股净资产是多少?16块钱,我不知道大家这里对财务有熟悉的吗?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那个时点股票的价格测算,我们每股一上来就亏了四块钱,但是如果按照净资产来算,我们一进去每股赚了八块钱,这两个办法来入账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这个方案小股东拥护,其实真正的这两个风险都和市场波动有关系,如果澳元一路跌下去,如果四块钱港元变成两块钱港元,那我们损失惨重。但是我们有一个判断,认为中信泰富除了这个事以外,其他的资产经营状况良好,所以我们有一定信心。

2008年金融衍生品引发的金融危机
当时做这个事的时候,王岐山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他管中央经营机构,我跟他当时有明确的表态,我说我身为董事长,虽然这个公司的经营我们管不了,它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但是既然出了这个事,请你问责我,摘我的乌纱帽。他说你少跟我来这套,你好好的拿出方案来,把它解决了。我说那你要这么做,我们就去拿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也要经过批准,后来我们成功了。股价没有多久慢慢就从四块八块一直到十三四块钱了,我们的心里就踏实了。
当时一路波动,六毛九,六毛八然后七毛一,我记得当时马凯同志在王岐山同志的办公室对面,他见到我说澳元已经七毛一了,都在关心一分钱,整个国务院的领导都在关注这个事。最后我们成功了,我们在澳元的基础上赚了六个多亿美元,我们赚回来了,我们在农行借款方面无论按照事实还是净资产都翻了一倍,赚了十五六亿美元,这是我们的一个案例。
后来人家说这是一个经典案例,让我总结一下,我总结了三句话,是从农民那儿总结吸收的——个人要努力,领导政策好,还得天帮忙。这个天是我们的客观外部环境和条件,其实是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强的能力,是中国的体制优势是的体现。
2008年11月,我记得在中央全会以后,和中国经济工作会议中间紧急召开了一个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这应该是真正的中国经验,虽然它有负面作用,比如说关于四万亿投资的一些损失等等,但是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改变了预期——当时东莞人都走光了,员工都回家的情况一举转变了。所以你看我们不是光靠自己,也不是光靠命,是靠国家发挥了作用,所以它就是我们的“天帮忙”。
所以我觉得你们各位在人生中将来做任何一件事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人不努力肯定不行,如果没有很好的政策环境,或者好的领导不行,但是没有机缘和运气也不行,这是我作为一个72岁的人的体会,你们将来都会尝到这个滋味。在2010年总书记跟我谈话的时候,我们的业绩大概就是这样的,我们2009年第一次进入世界五百强,415位,九年下来,现在已经是137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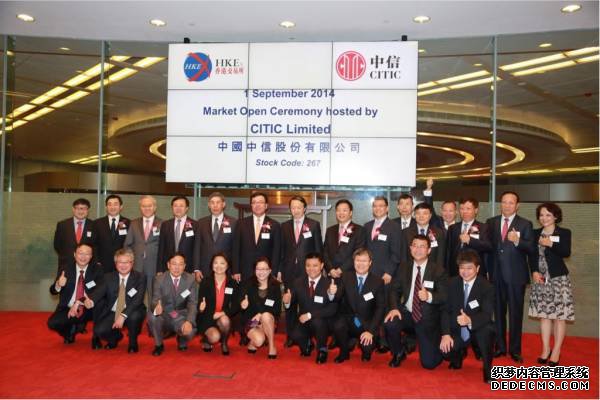
2014年中信集团整体上市
到2018年末我们总资产是七千亿人民币,我想提醒大家,最早开始给我们拨注册资产两个亿,最后没有给钱,荣老板垫了一千万,后来给了两千万,我们号称两亿起家——七千亿是两个亿的三千多倍。有的人一直坚持一种流行思维说国企低效、腐败、垄断,我们没有垄断性的行业,这个也不能说我们是低效的,当然我们遇到了风险,但是最终克服了困难。大家看我们的净利润从65亿,2007年189亿,2008年142亿,2009年189亿,我退职的时候是332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说这些是想表达,我们改革开放的历程是曲折艰难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按总书记说的让民族复兴,不可能是敲锣打鼓坐着轿子来进入民族复兴的大门,而是最近我们常说的,“船到中流水更急,人到半山山更陡”的情况。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我们七十年辉煌是一个非常一帆风顺的过程,这是一个理解上的误区。六十年代中国提出“小康”,到现在习总书记说“全面小康”,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我们中信的三十年出过一本书叫做《艰难的辉煌》,我相信大家听完我刚才讲的内容就会觉得原来中信也是曾经经历过如此艰难的时候,同样,光大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艰难的时候。
我的第四个时期是在我退职以后,2011年底,我做了一个事,这成为了我人生的下一个节点——我组建了一个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在中央领导推动下,我们中信集团作为国有集团承担政治责任的举措。我们的宗旨是三句话:“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我们要打造一个具有特色的民间智库,其中特别是我们提出的中国学派。
我有一个看法,我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学派,因为毛泽东不但是实践家,而且是理论家,毛泽东思想是哲学的,也包括一些经济学方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还包括战略学方面的,他应该算是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不是做学问的,但是他有很深的学术根基,还体现了理论的实践性品格,毛主席是近代现代的第一人。小平同志是实践性很强的,他推动了解放思想,他是一个推动者。
而现在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大家看得很清楚,他在理论上的推动作用,他的建树已经成为我们的引领者。我们时光过得很快,基金会建立到现在已经五年了,我们举办了124次活动,认领和承担国家部委交办的课题有49项,上报的国家智库研究报告41期,发行经济党刊67期。刊发了我们的一些内刊,改革发展与安全,88期,中国道路系列讲座57期,中国道路丛书36种,在习总书记的新年祝词时,他的书架子上能看到我们的书。2017年我们成为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一个培训单位,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大概有一百次左右。
人生就是这样走过来,它跟时代紧密相连。南怀瑾曾经给我写了一幅字,他写了辛弃疾的一段诗:“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我很喜欢辛弃疾的气魄,我们不需要那种悲凉,但我们应该有那种为国效力的气魄。另外我喜欢的一首诗,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喜欢这个诗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出一种情怀,他觉得国家的事情生死都要去应对,而不能因为给自己带来什么祸福,福我就趋,祸我就避。其实对我们来讲,大半生已经过去了,我当然还在努力,就像前面说到的“永久奋斗,奋斗至死”。

2000年,孔丹在香港看望南怀瑾老师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都是精英,在整个中国的十几亿人口里面,你们是极其优秀,也极其幸运的一批人。但是有一条很重要,你们要有家国情怀,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曾经有同学对我说“我们没有经历跌宕起伏的时代”,我说不对,你们面临着比我们那个时代更要紧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到了关口,是复兴还是倒在复兴的门槛上,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国家的整个发展大局需要大家的努力和智慧。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做到用学术来报国,我跟大家共勉。
在奋斗报国上,我现在还想干,你们干,我也干,我们一起来努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