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为甩锅自身抗疫不力,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部分政客和媒体借疫情大肆渲染“向中国索赔”的论调。在操弄政治议题的背后,我们应该如何从司法层面加以应对?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国内著名国际法、人权法专家戴胜教授。
[采访/观察者网 武守哲]
观察者网:戴胜教授您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采访您的机会。现在美国某些政客声称中国应该为美国疫情的严重而负责,鼓动“受害人”向中国政府索赔,背后还得到一批美国法学家的支持。此事本质上毫无疑问是个政治性的议题,但也触发了某些国际法的问题。从法理学角度上,您的看法是什么?
戴胜:人类在进入21世纪以来,首次面临着一个强大而又有很多未知病毒袭击的局面,在各国都在努力抗疫,尽可能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时候,美国跳了出来,谋划了一个所谓的“索赔”方案。这些索赔带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它不是针对中国民间的索赔。目前美国有四个州的州政府向美国的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比如佛罗里达州的伯曼法律集团(Russell Berman),还有前两天成为新闻热点的密苏里州,该州成为美国各州中第一个向中国追责的州政府,是他们州的总检察官提出的。从中我们看到被告的主体都是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第二,其中一个步骤是搞集体诉讼,通过一个网站进行团体认证,希望更多的“受害者”加入进来,这是诉讼前的所谓证据收集准备。
第三,这些诉讼所找的理由都相同,就是试图坐实我们是病毒的源头,比如生物武器实验室的活动等等,阴谋论地认为中国违背了一些国际公约。同时,这些诉讼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原告,现在还在征集中。
美国的律师把遭受到和预期要遭受到的损害都算在内了,比如“美国企业的收入和利润都大幅降低”,这些都是间接损失,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把它们列入赔偿的范围。总之,美国尽可能在从国际法层面上找所有诉讼的依据,比如WHO的章程条例,和IHR2005(国际卫生条例)国家义务的内容,甚至是某些国家不法行为,比如通过战争赔款的方式,都加入索赔范围之内。
美国国内的司法实践界和学术界对此是有极大争论的,大致分成了两派。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美国法律体系特色,从我们国家的角度看,无论是我们的《宪法》,还是其他各个重要的部门法,例如民法典,都尊重国际法优先的原则,国际法在国内法的适用上有一个转化和优先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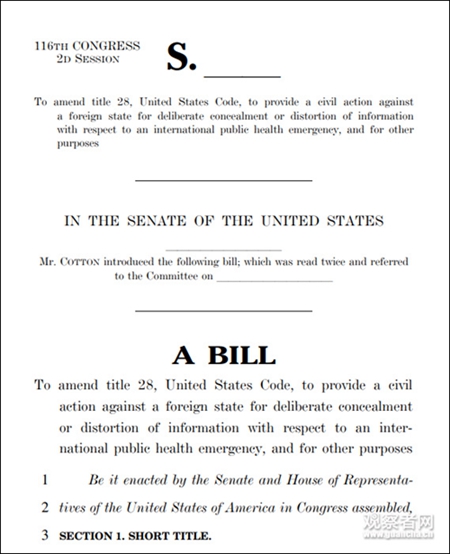 、
、4月16日,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科顿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丹·克伦肖发起草案,声称中国应该为美国爆发疫情而负责
但是美国的国际法原理跟中国不太一样,它讲究的是国内法优先原则,国内法优于国际法。对于美国本土的,无论是联邦系统还是州的两个平行的司法系统的法院,是否对外国政府或者是对某些主权国家拥有管辖权,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美国法案,就是“外国主权豁免法”。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法律界分为了两大派,一派认为他们越不过主权豁免障碍,主张广泛豁免,另一派以代理佛罗里达州的律师团为例,认为中国不能受到主权豁免保护,应该扩大或者改变现有的主权豁免条件,所以说美国司法界在学理和实践层面上,都是有争论的。
观察者网: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即“911事件”受害者家属诉沙特阿拉伯案,当时美国指控沙特政府涉嫌资助袭击计划,要求数十亿美元赔偿。沙特政府享有主权豁免权,虽然奥巴马本人表示反对,但美国国会还是为类似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
戴胜:我认为,不能要求中国的企业,或者是与美国相关有商业往来的国际大型企业,在我们国内向有关法院对美国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进行起诉,因为我们国家采用的是绝对主权豁免原则,所以民间企业是不可能在我国任何法院对美国政府进行起诉的。
我认为可行的对美起诉方案是基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合约关系,这一块我们是有操作余地的。无论是在合同的履行地,还是总公司在中国的分部,只要民事主体、行为等要素与中国有关联,那么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一般都会要求管辖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的法院是可以进行案件受理的。
另外一点,有没有可能去美国的法院进行诉讼?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中国的海外企业在美国的分部也涉及到海外资产和利益的问题,所以说根据美国的管辖权,也可以根据相应条款在美诉讼。
主权豁免主要分两大块:绝对豁免和有限豁免,我们国家采取的是绝对豁免,美国是有限豁免,有限豁免是有条件的。
我们法律界的专家,包括我们法学理论界的人士,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有这么几类观点:一些学者觉得我们可以高枕无忧,认为美国是没办法越过主权豁免条款的,他们认为,国际法体系长期以来都是基于“民族国家”主权原则,平等主体之间是不能够进行什么管辖的,只有平等交往,互惠互利。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国际法原则,所以现在很多专家认为我们没什么可担忧的。

前美国代理国务卿董云裳21日在华府智库“新美国”举办的“新冠疫情如何改变美中关係”网络对话会上,坚决反对剥夺中国主权豁免
还有一批学者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更多考虑到中美之间的利益联系,认为这次疫情加剧和放大了两国经贸的断裂感,不太愿意走出应诉这一步,担心中企在美国的一些利益会进一步受损。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美国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试图突破主权豁免原则。
那么,美国的法律集团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他们可以扩大对“豁免”的解释。沃尔曼法律集团认为中国政府不能受到主权豁免保护的主要原因,就是FSIA(Th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注:出台于1976年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案,)规定了两个例外。其中一个是有足够能和美国联系的商业活动;第二个涉及到领土侵权。在这两种情况下,外国政府是可以在美国法院被起诉的。现在情况来看,他们的诉讼请求是非常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难以证明符合这两个例外情况。
我们和疫情相关的医疗企业或者高科技企业是否有足够的涉美国际级的商业活动?他们从事的活动怎么能够被定义为领土侵权?他们要证明这些企业背后是有政府主导的商业活动,还要证明这些政府主导的商业活动是否和美国产生密切的关系;退一万步讲,行为本身和侵害的后果是否有足够的因果联系,这样一个侵害是否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是否能够适用普遍管辖原则?这都是需要用法定证据来证明的。
所以适用普遍管辖条款对某个国家是非常严重的指控,相当于说这是国际犯罪了,再往上就是说,这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的指控。
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了,有美国的国会议员希望通过立法或者修法的形式突破主权豁免原则,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还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正在试图完全破坏国际法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传统原则。即便是在国会立法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另外美国还有一些方法突破这个界限,比如说各州的立法,或者退出一些国际条约。
而且他们最有“杀伤力”的是立一个新法,比如最近国会两院在谋划一个博眼球的“为新冠病毒受害者追求正义法”。像这样的法不止一部,是一个系列,据我所知有五六部之多,都是由美国两院同时提出的立法草案。像这个“为新冠病毒受害者追求正义法”就突破了主权豁免原则,直接起诉中国要求赔偿,而且写明了赔偿条款,我们称之为牙齿条款。
而且这个法案还计划在美国国务院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对我们政府的防疫工作展开国际调查,通过单方面国内立法获得赔偿。另外美国各个州也有各种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立法, 比如《降低药品成本法》、《供应链安全法案》等等,开始做一些赔偿标准量化工作,煽动其他国家,采取一些公开的标准搞羊群效应,希望一些别的国家也按照这个标准对健康和经济损失进行评估,建立国家赔偿的机制联合对中国进行诉讼。
虽然他们这条路不一定走得通,但是挑起了一杆国际法诉讼大旗,他们以国家安全、人权、甚至以国际突发事件为借口,授权美国总统展开“独立调查”,这对我们是一个潜在的危害,即在美资产被冻结,或者征收特别关税的危险,所以说这一块我们要特别关注。
还有一条路是搞单方制裁,但这个需要走联合国安理会的程序,而我们是五常之一,所以安理会程序上是通不过的,但有没有另起炉灶的可能?比如美国刮起的这一轮诉讼风暴会威胁在全球市场上和中国脱钩,为下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加码。我们现在处在全球化领导权的过渡期,中美是否要走进修昔底德陷阱?在这些判断之前,我们必须要认真应对这次诉讼潮,减少国际舆论对我们不利的因素和政治资源上的负面影响。
我们看到,今日美国法律在技术层面上已经变得非常工具化了。美国的一些政客堕落了,现在美国的立法权也开始堕落了,甚至是美国的职业律师也搞出了这样的非常丧失职业精神的事情,他们明明有健全的国际法常识,却冲在这些有争议性的一线政治操作中,任何一个有职业素养的美国律师都不会这么做。
对此,我们希望美国的司法机关还能保有一点“司法独立”的底气,遵守一些国际公约,守住正义的最后一条底线。美国的司法权曾经被称之为“最不危险的权力”。但是每一次美国的重大社会变革,往往不是由立法权,也不是由行政权,而是由最不起眼的司法权来推动的。美国的教育平权、同性恋、堕胎等案件都是这样的。如果美国这一次要冒险突破现有国际法的某些基本原则,就有可能改变整个美国,乃至世界法律实践的格局,我们应该特别关注。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美国正在搞羊群效应,拉拢其他国家。现在意大利、英国民间等等也出现了向中国索赔的声音,他们是不是必须要依附于美国,否则按照他们各自的国内法,是进不到正常的诉讼程序的?
戴胜:今天我们所看到主权豁免,包括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例如穷尽国内救济原则,都来自于欧洲,我们期望他们还能遵从国际法传统。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所确立起来的国际法公约体系,比如说维也纳公约等等都起源于古老欧洲,所以他们有保有守护国际法之主权国家平等交往原则的情怀,我们希望他们能守得住。他们是否要跟着美国走,我看也不一定,因为这里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区别。
大陆法系认为不能临时制定一个新法来追溯既往,不能通过即时性的法律来追究我前面行为的一些责任,这是违背现代法律基本原则的。
而且欧洲国家必须要遵守穷尽国内救济的原则,比如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境内没有出现告中国这样的案例,获得最终判决之前,是没办法提交到区域性的国际人权法院的。目前欧洲人权法院机构改革积案数量也比较大,我想他们也是自顾不暇。
所以我想他们也只是在舆论上跟随美国,而不会落到实际的具体司法操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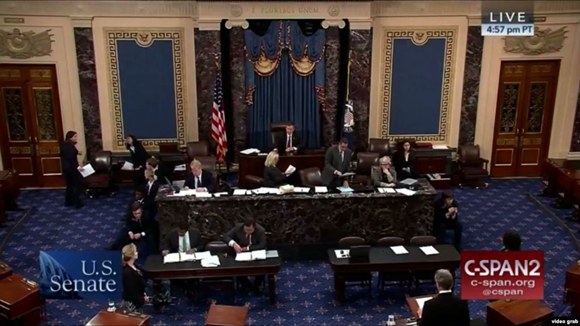
2018年12月11日,《西藏旅行对等法》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最近这两年,美国参众两院出台了一系列损害中国主权的法案,如《西藏旅行对等法》、《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台湾安全加强法》等等。这些法案的出台和如今的对华诉讼本质上是否都和美国所谓的“长臂管辖”原则一脉相承?
戴胜: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通过所谓的单方国内立法,形成独立调查机制,然后用所谓的独立调查员的报告向美国两院发起制裁计划,之后两院再出台相关经济和政治上的制裁措施,由美国相关的行政机构加以执行。同时这也是美国地缘政治的新设计,通过设置这样的一个议题,比如涉港和涉台的人权和区域安全问题,希望他们的盟友跟进,然后再从中挑拨离间,无论在传统还是非传统的区域安全地带,美国都会见缝插针去做,所以美国可能还会修订前面的一些法案,或者增加这些地区的所谓受害人求偿条款。
美国现在所做的不仅是民间集体认证,它们还抓住我们在抗疫过程中一些极端的个案,来进行所谓的受害人赔偿,这值得我们警惕。
观察者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咱们中国受损的企业可以向美方提出诉讼,从程序上讲,是不是类似于跨国公司那种商业纠纷的模式?
戴胜:差不多应该是的,我一直持这样一个态度,即我们不能一味地觉得可以有主权豁免就高枕无忧了,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来,我们认为美国不敢做不能做的事情,他们现在都在做了;
第二点,我们也不要患得患失,认为启动诉讼会损害中美关系什么的,这只是正常的权利救济和法治保障方式。更不要卑躬屈膝或者沉默是金,因为很多事情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做的,我们在抗击疫情,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和履行国际义务方面是有证据、有事实、有底气、有依据,是可以去提起对美诉讼的。相反,如果他提起诉讼你缺席审判,就好像本来我们有理的事情变成了理亏的事情,在法庭的规则之下其实是一种能力不足的表现,你就会丧失宝贵的法律救济机会。这就是我坚持认为接下来我们要勇敢地走出去,因为你不走出这一步,永远都不知道失去了什么,或者是能够得到什么。我们不能让我们中国的国际法课程永远停留在课堂上和教科书里,我们太缺乏这样的国际法律师团队了。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医疗团队和技术团队送到国外实施援助,现在到了我们的职业国际法律人走出去的时候了。当然我们知道和美国的一流律师团队过招,差距还很大,但是我们应该去实践一下,走出这一步。
至少我们可以首先计划征集集体诉讼,对美国某一个官员提起诉讼,这样可以保护我们在海外企业的利益,甚至可以保护我们海外公民甚至是华裔的生存权和各种利益。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美国的抗疫过程就出现了种族主义污名化的倾向,让在美中国公民,包括华人华裔群体在许多民权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甚至是歧视,而且我们也可以尝试找美国的职业律师集团和律师事务所代理我们这样的案子。
我们国内的专家可以认真研究民事商业诉讼案应该如何操作,状告那些美国公司,借口中国疫情公然违约,终止合作,违反技术转让、商业义务的一系列违法行为;登记与美国有紧密商业联系的这些公司、企业和个人,为受害者解答法律问题和起草起诉书,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要学会拿起国际法的武器,有一句话叫谣言止于智者,还可以补充一句,诉讼止于证据。我们应该自信可以做这一系列事情,未来很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法律诉讼或非诉的风险和困难,也可能在法律的技术操作层面上,现在看起来还有些不切实际。但是你会发现美国的司法界,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主动创造条件去突破主权豁免,所以我们不能拿着法律技术层面上的障碍当“护身符”,做好最坏的打算,但一定要有最优最精细的迎战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