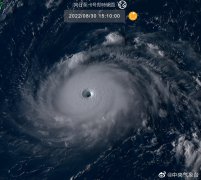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我们见到了一群80、90后,他们是这里的修复师、临摹师、研究员,以及展示交流员。来这里入职前,他们有人大学刚毕业,有人经历过创业的成功,有人在富士康流水线当工人,还有人离了婚辞了安稳的工作。
研究所远离城市,他们无一不是在年轻时就当起了石窟里的“面壁者”。有人从4800公里外的福建沿海来到这里,像种子寻到沃土般,在龟兹壁画这棵大树旁扎了根;有人则是在长久的“面壁”中发现,这些石窟里的壁画是“有温度的”,它的残破中隐藏着来自1700年前的丰富信息。
在克孜尔孤独而漫长的时光里,他们常常被问到,留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能离群索居地坚持这么久?一些意义藏在细节里,例如出差返回,看到茫茫戈壁中那片绿洲上的石窟时,内心莫名地兴奋。或是一个曾经离职的员工,告别时,看到好几位同事眼含泪水,才发觉有些连接很难割舍,后来他又回来了。
 研究所的修复师正在养护石窟
研究所的修复师正在养护石窟
遇见
7月末的新疆,上午10点不到,阳光暴晒着石窟工作站的矮房。修复师杨杰从房间里走出来。他穿黑色短袖T恤,戴白色防晒袖套。下身的工装裤和短靴是发旧了的灰黄色。
屋外树下停放着一辆白色面包车。杨杰等修复师们和4名实习生都上了车,才和另外两个同事背朝司机挤在了摆在后备箱的小板凳上。这车是他们从工作站到石窟间唯一的代步工具,人多时,座位就不够用了。引擎发动后,车驶出工作站,过石窟保护区的大门,随后在灰黄色的群山间缓慢前行。
20多分钟后,库木土喇石窟到了。正值旅游旺季,但这里尚未对游客开放,四周只有公路和戈壁滩,手机在这里收不到信号。刚刚结束上一个修复项目,杨杰他们这次来库木吐喇石窟,是为了配合这里的开放计划,对石窟进行日常养护维修,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去除失效的历史加固和治理壁画局部较严重的病害。
目前,这处石窟和克孜尔石窟等9处石窟群,均由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保护和管理。研究所设在克孜尔石窟景区内。“克孜尔”就像是这些年轻人的“大本营”,保存着349个洞窟和近4000平方米的壁画。约公元3世纪至公元8、9世纪,古人在这里开窟造像,克孜尔石窟是我国现存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
历史上,它曾遭遇西方探险队的劫掠。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英、法、德、日等国的探险队先后到克孜尔石窟,带走了大量壁画、彩塑等珍贵文物。其中,德国探险队揭取的壁画面积近500平方米。
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些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开始得到关注。新疆龟兹研究院(即今天的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先后奔赴多个国家,经过20年的努力,收集到8个国家20余家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的470余幅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高清图片。借助数字化等技术,大部分的壁画已经找到其所出洞窟及被切割的位置。
然而,现存原址的石窟壁画仍面临着诸多病害的侵袭。包括杨杰在内,研究所8名修复师的工作,主要是围绕9处散落在茫茫戈壁滩上的石窟群开展的。
洞窟内墙壁上一些曾为保护壁画而涂抹的水泥,已失去了应有的保护作用,且会对壁画长期保存产生不良影响,需要想办法去除掉。墙壁上现存的壁画,局部存在地仗层酥碱等病害,地仗酥松,需及时治理。一些壁画地仗层边缘跟岩体已经分离了,有脱落的隐患,也需要进行针对性保护处理。在进行壁画回贴时,需要先把背后岩体清理干净,然后用加固材料对岩体进行加固,再填泥回贴地仗层。这些都是为了让壁画保存得更久一些。由于和泥土直接打交道,从洞窟内出来时,每个修复师身上都落了灰。
杨杰201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专业,那年8月,他入职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在他看来,这里的壁画漂亮,资源丰富,但保护力量相对薄弱,相关设备、数据和资料都是匮乏的,需要专业人员。
那时,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的保护部门刚成立,基础条件落后,人才匮乏,很多事情杨杰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现实的另一层面,是自然的不可抗力。一些洞窟,如库木吐喇石窟的第15窟,病害比较严重,有的壁画已经剥落悬空,地仗层疏松,“一摸就掉”。“如果是用病人来形容它的话,它应该已经是癌症晚期了。”杨杰说。而修复师则像是医生,他不能保证让“病人”恢复原貌,只能尽量延长它的寿命。
因石窟开凿在砂砾岩的崖壁上,岩体稳定性较差。如果再遇到春季冻融交替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发生局部岩体的掉落。在克孜尔石窟开展岩体加固之前,每年春季进行石窟巡查时,经常发现有掉落的岩块。“看着这些掉落的岩块,作为一名文物保护者,总会有无力感和挫败感,”修复师周智波说,“会觉得在自然规律面前,自己很渺小,需要我们进行有效应对时,力量又那么有限。”
 克孜尔石窟的菱格画
克孜尔石窟的菱格画
在克孜尔石窟研究所,临摹工作是对壁画艺术的另一种保存。临摹师们坐在洞窟内和画室里,将壁画内容临摹在纸和泥版上,让艺术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得到延续。
临摹师梁观忪的大学是在厦门读的,专业是油画。2010年,还在读大三的他第一次来新疆克孜尔石窟。他刚开始很兴奋,上百个洞窟,挨个看下去,但看到两天半的时候,他觉得受不了了,那些洞窟和壁画好像能把他“吞掉”。
克孜尔的石窟内有大量菱格画,每一个菱格画里是一个佛教故事。菱格画遵循着某种强烈的秩序:绿、蓝、白、黑等颜色反复出现,但重复中又都不一样,这让他产生强烈的视觉压迫感,“你无法想象古人为什么花这么大精力来做一件重复性这么强的工作,他到底要干嘛,你(当时)没有概念”。
在梁观忪看来,克孜尔石窟壁画和今天的互联网很像,“壁画风格受过犍陀罗的影响,也受过中原地区的影响,是好几种文化在这个地方生发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文化高地”上汲取到丰富的营养。但在刚来的两年时间里,面对这些壁画,他觉得迷茫,找不到切入口。
要研究、解读这里的壁画,存在着很多障碍,“你研究敦煌,还有唐代出土的经书,大体还能看到粉本,但这啥都没有,就剩下断壁残垣和一些壁画。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古龟兹人是怎么画的,他们的手稿是什么”。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明屋塔格山的断崖上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明屋塔格山的断崖上
“劝退”
梁观忪是福建人,家乡临海,刚来研究所入职时,克孜尔正值早春,天是灰蒙蒙的,还有沙尘暴。他被那种灰色压了整整一个月,感觉人快崩溃了。
在克孜尔,“面壁”的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这样的“灰色”时刻,而每个人决定留下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来研究所的第一年冬天,有次单位搞活动,沙娜找了个机会溜出来,给父母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说自己可能待不下去了。妈妈劝她说,待不下去就回来吧。“但当时我又想坚持。可能时间也长了,又遇到穆林肯了,就真的留下来了。”沙娜说。
沙娜是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信息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丈夫穆林肯在遗产展示交流中心工作,两人2017年入职,都是90后。
研究所里面和周围没有奶茶店和面包店,也没有小卖部、超市。这里拥有的是鸟叫,虫鸣,以及偶而出没的黄羊、野猪、狼等野生动物。离这里最近的城市——库车市市区,在60多公里外,而这段路没有公共交通。每周,研究所会发一趟往返库车市区的班车,员工可以搭车进城采买。每次去库车,沙娜和穆林肯都会“报复性消费”一番,吃顿大餐,点上好几杯奶茶,最后再去超市买齐一周要用的东西。
 穆林肯与沙娜
穆林肯与沙娜
想要留在克孜尔,就得学着适应孤独。穆林肯对抗孤独的办法是跑步。傍晚,结束工作后,他会沿着研究所里的林荫路,独自跑完一整圈。在克孜尔孤独而漫长的时光里,除了临摹工作,梁观忪还学会了写书法、刻印章、做漆器和补茶杯。
前几年,梁观忪去上海一个发小开的公司,跟一群90后的员工聊天时,感受到了某种紧迫感。他发现,外面世界的年轻人,头脑活络,接受资讯更多、更快,创造力也强。“我就感觉我自己在这待着,已经快被时代淘汰了”,他那时候就想,“我能跟他们拼什么呢?”他能想到的是,“把自己专注的事情做好。”
在杨杰看来,在克孜尔,“生活造成的困扰更大一些”。他还记得刚来克孜尔时的情景:生活用水是从河里引来的,发洪水时就会停水,一停就是一个星期,没地方洗澡,来水之后,水里也全是泥;宿舍人多床少,铺位不固定,他又常去野外作业,只能哪里空就睡哪儿,他几乎把所里铺位全睡了个遍……
有一阵杨杰想过离开,但遇到了一个同单位的女孩。后来这女孩成了他的妻子。“阴差阳错”的,他还是留在了克孜尔。
结婚那天是冬天,室外温度达到零下一二十度。妈妈从老家云南来新疆,第一次穿上羽绒服,一直在说,“这么冷的天!咋待呢?”直到现在,每次和妈妈通电话,被问到什么时候回家,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父母把你养这么大,你跑这么远,他们现在身体好还好,要是身体不好你回趟家都困难,这事有时候想想,挺难的。”他工作的石窟,到现在还没带妈妈去看过。
和杨杰同一批入职的人,“现在可能走了有一半了”。有几次杨杰想要走,冷静下来,又觉得不舍,“你在这个地方待出感情了,一想到要离开这个地方,可能这些人跟你也没什么交集了”,杨杰说,他这十年来最好的朋友都在这里。
修复师周智波也曾动过想走的念头。当时,他已经在西安安家,孩子由老人在西安带在身边。有一次,周智波的妈妈住院了,他刚好在兰州学习,就请了几天假回西安探望。那时,他的大女儿1岁多,刚学会说话。他给女儿买了串她爱吃的葡萄,回去老人问,葡萄是谁买的,女儿指着他说,“这个叔叔买的”。他心里觉得对家人很亏欠。
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周智波的妻子放弃了在西安的工作,和他一样来到克孜尔工作。今年上半年,夫妻俩把两个孩子从西安接来新疆库车上学。
 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在茫茫戈壁中的一小片绿洲上
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在茫茫戈壁中的一小片绿洲上
惦记
周智波有时去外地出差,回来研究所,车驶过灰黄色的群山,一转弯,茫茫戈壁中那片绿洲上的石窟陡然在眼前铺展开来时,他总会产生一股莫名的兴奋感。在研究所,他没事时就会“上洞窟”,看看那些“生病了”的壁画。别人和他聊天,总会觉得无趣,因为他“说话三句里有两句是关于壁画的”。
刚来研究所那年,杨杰作为修复学徒第一次上手,是给壁画做清理工作。探身进入库木吐喇编号为58的洞窟门,左转仰头,那里壁画的一角,是杨杰那段时间每天爬上脚手架,“蹲了”半个月清理出来的。
“刚开始也会烦,也想学点别的”,杨杰说。不过,一旦让自己沉浸在具体的事里时,他就找到了成就感和乐趣。
杨杰清理的这块壁画旁的窟顶上原本有一个大裂隙。裂隙漏水,形成泥渍,把壁画盖住了。清理原则是:愈靠近壁画,愈要小心。厚一点或硬一点的覆盖物,为了保护壁画颜料,不能一次性去除干净,只能用竹签或油画刀小心翼翼地逐层剔除,有时也需要特定的试剂先润湿软化;剔到只剩一两毫米时,再用棉签轻轻滚动,将覆盖物清除。
小竹刀,通常都是自制的,将竹筷子较粗的一头削薄,在砂纸上打磨光滑而成。像这样自制的工具,在他们日常使用的工具中不在少数。
杨杰有时候觉得,清理壁画有点像 “刮彩票”。在刮奖区“灰黑色”的覆盖下,意外清理出一尊小坐佛、一块精美的装饰图案,内心惊喜又满足。往后的岁月,这样小小的成就感曾如烟花般点亮他在洞窟内与壁画为伴的生活。
 张婷在讲解克孜尔石窟38窟的壁画
张婷在讲解克孜尔石窟38窟的壁画
转岗到研究所的遗产展示交流中心之前,张婷是这里的一名临摹师。张婷研究生学的是国画专业,她还记得自己临摹的第一幅壁画——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一幅闻法天人。
初见这幅闻法天人,她觉得造型极美,但不可思议的是,天人一只手竟有六指,“我还愣了呢,说这为什么是六个指头,一定是画错了吧”。
后来有次,张婷给游客展示作画过程,用的恰好又是38窟的这幅闻法天人。已经有了多年的临摹经验,她发现这次的感受和第一次完全不同:“这次就理解了,(画师)起稿的时候画错了形,但是最后完成的时候进行了复勾,原来画的线条也保留了下来。在作画时他是一气呵成的,人物呈现出的是一种动的状态。在临摹时你要把这个动的状态给抓住,才能画出你想要的效果”。
面对研究资料不足,梁观忪发现,最简单的办法是从“现象”入手:例如,先研究古代画师作画时用了哪几种材料。在壁画颜色脱落地方,研究色彩的层位关系,看哪一层材料在上,哪一层材料在下。然后,自己动手去做颜料。等这个阶段度过了,就开始研究人物造型特征。“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得惦记着它,一点点抽丝剥茧,一点点寻找”。
 库木吐喇石窟内的壁画局部
库木吐喇石窟内的壁画局部
连接
修复工作做久了,杨杰越来越觉得,洞窟内的壁画是有温度的,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壁画上很多微小的细节,只有进洞窟仔细看才能发现,光靠电子扫描的版本,可能是找不到的。
他和同事们发现,一些佛像袈裟上贴的“金箔”有被人抠掉的痕迹。那些叶片状原本贴有“金箔”的地方,仅残余一点点的“金箔”,如果是在电子画面上很难发现,“需要(通过)实物去感受”。
他们还发现了壁画上有可能用过其它箔来模仿金箔。“有些佛龛里的贴箔区域,局部看它是金色,但是你用便携X射线荧光光谱仪(一种便携仪器,可以分析物质的元素组成)进行无损鉴定就会发现,它的主要元素是锡,古人可能用锡箔辅助特殊工艺来仿造金箔”。
除了金属箔这种材料,他们还研究了贴箔的工艺,发现金属箔是用一种虫胶贴在壁画上的,和颜料用的胶不一样。从虫胶延展开来,还可以再研究其在新疆或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这就越来越有意思,一个小小的点可能激发出来很多的东西。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我们可以实现和古代龟兹艺术的创作者‘对话’,这也能帮助我们更科学地保护他们所留下的文化瑰宝。”杨杰说。
 杨杰在检查石窟里壁画的状态
杨杰在检查石窟里壁画的状态
研究清楚壁画使用了哪些材料和工艺,不光有利于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修复,也可以服务到复原性临摹。“像临摹师做壁画临摹,其实很少有人用到像这些金属箔的装饰,这些如果没有做,那这个临摹工作是不是不完整的?”
梁观忪曾临摹过一张《汉风菩萨》,临摹时反复改稿。“其实每一稿的差别,可能就是那一丝,几微米都不到,两个放一起感觉是重叠,但是不是。”他说,这样做是为了练习“准”的功夫,例如,两根线条形成一个嘴角的弧度,这个嘴角的弧度到底多少?“有时候可能跟壁画上就差一点点,但就那一点点可能出来的神情和面貌状态还是不太一样”。
临摹库木吐喇新2窟穹顶的13尊菩萨时,需要把穹顶图转换成平面图。“从梯形的边变成平行的边,人物势必会变形,上面会变大,底下会变小。所以就需要把人体的比例关系重新组合一下”。
他在思考,让壁画这种古老的石窟壁画“移步”现代居住空间,应该怎么样来呈现。穹顶中,有的菩萨残缺了一只脚或其他部位,临摹补全时,他需要“根据脚和头的比例来定”,“做每一步都是有考量的”。
这种理性不仅被他用在临摹工作中,也体现在职业选择上。9年前,梁观忪大学毕业。来克孜尔之前,他先是在厦门创业两年。初出校园,创业帮他赚到了钱,也让他离“(在社会)变得有用”的目标更近。有次,启蒙老师和他聊起画画,他才意识到,自己一年也没几张作品,离自己坚持了很多年的专业越来越远了。
恰逢那个时候,他看到了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的招聘。被录用后,他像种子寻到沃土般,来了龟兹壁画这棵大树旁,也重新回到了画画这条路上。
在克孜尔,梁观忪发现,古代龟兹厉害的画师,能够从绘画的细节当中,让人感受到他在生活中有非常严谨认真的观察,然后再把观察的经验用到具象或表现的画里,“他做的很真诚”。
在他看来,很多时候,真诚是比技术更重要的东西。“大家都会用好不好、美不美来衡量一个艺术品,但是很少人会用作者花了多少心力来衡量”。他解释,心力就是作者灌注在作品里的执着与真诚。心力是最熬人的,但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他临摹时有个习惯,一旦某个窟有一张画打动过他,他就会花几年的时间“死磕”这个窟,尽可能把窟内的壁画都临摹一遍。面对壁画,他很在乎能触动自己的地方。
在克孜尔,“面壁者”要学会和1700年前的壁画对话。
一块“衰老”的壁画,因为年代久远,表面颜色都已脱落,只剩下一片白,但这白色可以带给梁观忪极丰富的信息和联想,譬如那里面有许多色彩存活过的痕迹,或轻盈或厚重。“你要沉下心来去和它对话,去观察它,找到那个触动你的点”,他说,尔后, “当你面对一张纸的时候,你要起心动念画的时候,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真诚,要很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