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文化全球化与比较文学在多元化语境下的发展,文学在空间压缩、地域联结上的特点愈发明显。比较文学本身是西方的舶来品,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兴起,吴宓于1924年在东南大学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等讲座,特为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先后又开设多门课程,意味着比较文学正式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当中,同时也体现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世界化的进程从此开始。之后又出现一批研究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的著作与论文,例如法国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由傅东华翻译,视为中国第一本比较文学译著。这一标志体现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产生阶段性的成果。然而在中国古代,最迟在汉代,比较文学就已萌芽,但有“比较文学”之实而无“比较文学”之名,直到近代以来才确定学科名。就同中国古代的名实学、小学,直到近代以来才以西方名词“逻辑学”、语言文字学名冠之。(1906年章太炎在《国粹学报》第二十四、二十五期上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又金岳霖出版《逻辑》视为两大学科名锤定之标志)纵观整个古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具有两个明显特点:
1、内容丰富,对于跨国界、民族、语言、学科研究成果尤为突出,例如两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译介学研究。
2、专业意识淡薄。西晋佛教学者讲解佛典时,常用“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的“格义法”进行阐发。
两晋南北朝时期没有“比较文学”这个概念,但在译介与格义阐发的过程中自然融入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产生“商略同义”的情况,影响后世。学界在此方面的研究上成果不是很丰硕,佛教《譬喻经》“梵志吐壶”与《续齐谐记》“阳羡书生”二故事即是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成果,笔者拟从二事中,,探寻中国古代比较文学的异同性与典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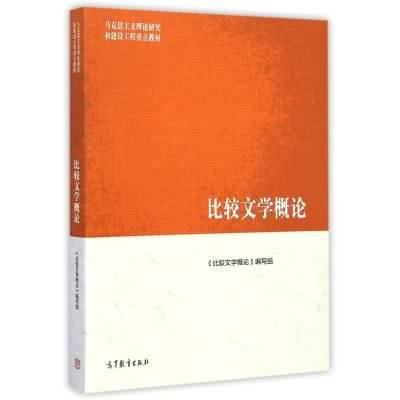 比较文学概论
比较文学概论
一、“繁志吐壶”与“阳羡书生”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角度叙事
“梵志吐壶”的故事出自印度佛经《旧杂譬喻经》卷上第二十一则《王赦宫中喻》,原文如下:
“昔有国王,持妇女急。正夫人谓太子:“我为汝母,生不见国中,欲一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则听。太子自为御车出,群臣于道路奉迎为拜。夫人出其手开帐,令人得见之。太子见女人而如是,便诈腹痛而还。夫人言:“我无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当如此,何况余乎!夜便委国去,入山中游观。时道边有树,下有好泉水,太子上树。逢见梵志独行来,入水池浴。出饭食,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女人,与于屏处作家室,梵志遂得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年少男子,复与共卧。已便吞壶。须臾梵志起,复内妇着壶中,吞之已,作杖而去。太子归国,白王,请道人及诸臣下。持作三人食,着一边。梵志既至,言:“我独自耳。”太子曰:“道人当出妇共食。”道人不得止,出妇。太子谓妇:“当出男子共食。”如是至三,不得止,出男子共食。已,便去。王问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欲观国中,我为御车。母出手令人见之。我念女人能多欲,便诈腹痛还。入山见是道人,藏妇腹中,当有奸。如是女人,奸不可绝。愿大王赦宫中,自在行来。”王则敕后宫中,其欲行者,从志也。师曰:“天下不可信,女人也。”
此记载点明了“阳羡书生”故事产生的渊源,吴均误认为“吐壶”是一种志怪的形式与方法,这是由于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一种误解。印度的法典《摩奴法典》规定,婆罗门青年有一个阶段的学习期,被称为梵志期,学习时,“青年学生应该按照法律进行盥漱后,面北,向圣典致敬,穿着清静的衣服,抑制情欲来受课”、“学生要在洗漱后,身洁心静地,在没有污浊的地方,按照规定,在日出日落时低诵娑毗陀利赞歌,完成宗教义务。”这就规定了青年在梵志期要严守规定,不能触犯戒律,否则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戒赌搏、争吵、诽谤、诈骗;戒含情凝视或拥抱妇女,戒损害他人”、“要经常睡在僻静地方,决不可出精;因为如果纵情恣欲,如果出精,就破了本种姓的誓戒,应该从事苦行赎罪。”
从法典中可以了解到,在梵志修行期间不能近女色,不可放纵自己的欲望,但故事中的梵志却私藏女人,并且和他淫乐,这触犯了法典的规定,因此他为了怕受到惩罚,把女人藏在了壶中以逃避自己的罪责。妇女在印度地位低下,并且在《摩奴法典》中,女人被视为情欲的化身,会严重破坏修行:“在人世间,诱使男子堕落是妇女的天性,因而贤者决不可听任妇女诱惑。因为在人世间,妇女不但可以使愚者,而且也可以使贤者悖离正道,使之成为肉欲和爱情的俘虏。”故事中的女人又在梵志睡着的时候,又吐出一个男子与他通奸,犯下了不贞与淫乱的双重罪责,女人明知犯罪,却用壶把男子藏起来借此逃避惩罚。最后通过王子的偷看揭发了这些行径。
 续齐谐记
续齐谐记
这个故事采用了空间与欲望的双重叙事结构,吐壶、通奸这些意向,无一不包含着宗教道德伦理的意蕴。佛经故事的主旨是对人,尤其是对女人情欲的贬斥与否定,“壶”是用来私藏女人的容器,象征人们隐秘情欲的内心。
而这则故事通过译介、翻译流传到中国,由于文化不同,自然就了解不到故事中隐喻的深层意蕴。晋人荀氏作《灵鬼志》时吸收了“梵志吐壶”的部分剧情,作出了《外国道人》一篇,这篇故事的情节是外国道人凭借幻术,愚弄吝啬的富翁,人口中吐出异性也只不过是情节的一部分,但是利用的却是幻术,原本故事中蕴含的情欲,经过国人文化意识的同化后,已经荡然无存,原本内含的佛教教义也不复存在,只留下了当时国人,或者说当时整个的社会意识形态最为关注的“道德问题”,而劫富济贫取代性欲,成为这一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
吴均《续齐谐记》中“阳羡书生”的故事也是,虽然借用了“梵志吐壶”的故事框框架,但已经完全没有舶来品的影子: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馔,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铜物。气味香旨,世所罕见。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心,情亦不甚,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邪?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彦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
这一故事同样缔造出一种怪异的空间感,吴均为了增加故事的真实性,把“梵志吐壶”中不曾明确的姓名、籍贯及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清晰的写了出来,故事讲述了书生许彦在旅途中道逢一位能入鹅笼中的书生,并且书生口中能吐物、吐人,吐出的女子口中亦能吐出一男子,男子口中又能吐出一妇人。这一系列变化较前两作来说,更加失了内涵,既没有揭示人内心的隐秘内涵,又没有愚弄富人、劫富济贫那样的道德问题,纯粹是为了故事的奇异性和可读性而刻意去编造的故事,丧失了前两则故事中“寓言”的内涵。也从侧面揭示了域外作品在翻译和译介到本国之后,由于国别文化的不同,对于作品的解析和理解也不同,因此时常会让人产生“奇怪”的想法,认为这些故事只不过是“志怪”而已,因此在南北朝时期,比如《搜神记》、《述异记》、《玄怪录》等志怪小说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域外作品流入中国,本国的作者受到启发,从而创作出这些作品。他们既不了解域外的文化习俗,也不了解作品背后蕴含的深层意蕴,又因为没有系统的研究方法,从而导致比较文学在中国虽然很早就出现了,但一直没有大的进展或突破,就是因为没有国际眼光和系统性的研究法。
又阿拉伯神话《一千零一夜》中有山鲁压尔和沙宰曼的故事,与“梵志吐壶”一脉相承,情节几乎一模一样,故事的结尾用诗歌反复强调女人不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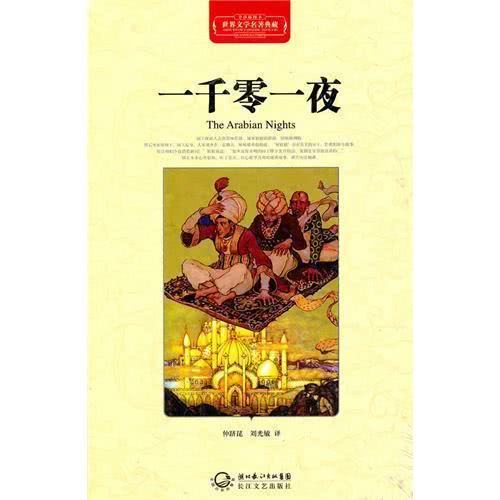 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
不少翻译研究者在考察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存在的事实上的关系时,自觉地关注某一文学文本,通过翻译的中介,在另一文化语境中的接受和传播,从而使得翻译研究中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的因素大大地增多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由读者对之主动接受和创造性阐释有关,中古时期的志怪小说就是由此而来。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外文学家和学者对吸收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