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人》

内容简介
《武汉人》是作家方方所写的与武汉有关的随笔集,书写了这座城市的故事: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到别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小事;从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到豪放直爽的武汉市民;从武汉的历史传说,到武汉人的现实生活、方言特色、吃喝玩乐……
作者简介
方方, 1955 年生于南京,长期居于武汉。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中篇小说《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桃花灿烂》《奔跑的火光》,随笔集《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等。多部小说被译为英、法、日、意、葡、韩、西班牙等文字在国外出版。代表作《风景》《琴断口》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其他作品亦多次获得国内各类重要奖项。
书籍摘录
行云流水的武汉
一
我想,我们坐在长江的入水口来说武汉是最好不过了。
这儿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汉水带着它的明亮,缓缓汇入浑浊的长江。入江口的水线十分清晰,两水激荡着状态,是又排斥又交融的。你细细凝视时,心里会蓦然地生出感动。
在这里,我们可以坐在江堤上,遥看龟、蛇两山的行云,倾听长江滔滔的流水。还有白云黄鹤、琴台知音这样美丽的传说和晴川汉阳树、芳草鹦鹉洲这样雅致的典故相伴在我们的身边。虽然它们与我们相隔了几百年甚至一千年,可此时此刻,你不觉得它们都近在咫尺么?诗说,“日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这诗就是站在黄鹤楼上写的。黄昏的这个时刻,读了这样的诗句,不觉得我心你心还有诗心都是相通的么?
这一切,对于一座城市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它们使这座城市的韵味绵长,自有一种动人的魅力温暖你的心。坐在这里,我们信手指点,它们便都会从四面八方、从千年万年的时光中,涌来眼前。
当然,我引你来到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是沿着这条大江,来到了这座城市。
二
那是 1957 年一个很冷的日子,我的父亲为了参加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带领着我们全家溯江而上,从古都南京迁来了江城武汉。
三轮车拉着我们来到一个名叫“刘家庙”的宿舍。这里刚刚建起十六栋红色的楼房,在周边绿色的菜园和开满着小小花朵的野地包围下,在竹林和低矮的冬青树的簇拥下,这红色的楼房真的是十分灿烂明媚。
我们搬入了刘家庙宿舍五栋楼上十一号。这个地址我们用了将近三十年。
我居住的这个刘家庙宿舍在汉口的东北方向,人们管这一带也叫黑泥湖。打起仗来,这里是进入武汉的通道。辛亥革命时,民军就曾与清军在这里打过一场大仗。所以,我小的时候,在这里看到过许多的碉堡,它们颓败地立在路边或树林里。
因为武汉曾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所以它四周的湖泊星罗棋布。我们宿舍的周边,也到处可见水沟和池塘。它们就是那些萎缩或分解了的湖泊。
现在我曾经住过的小楼已经被拆了,四周的湖泊也被填实了。大雨回来时,循着自己的记忆,找不到自己以前流淌的家,就在街上泛滥。而我也跟雨水一样,在这里已然找不到家了。这里的一切都在四十五年间改变了样子。昔日的田园风光早已不在。我住过的那一幢幢红色的楼房,都已拆毁。当年的年轻的意气风发的邻居妈妈们,业已老态龙钟。岁月虽然改变着环境,但它更着力改变着的是人的容颜。环境可以一天天地新起来,而人们却只能一天天地老下去。重新返回这里,我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些惆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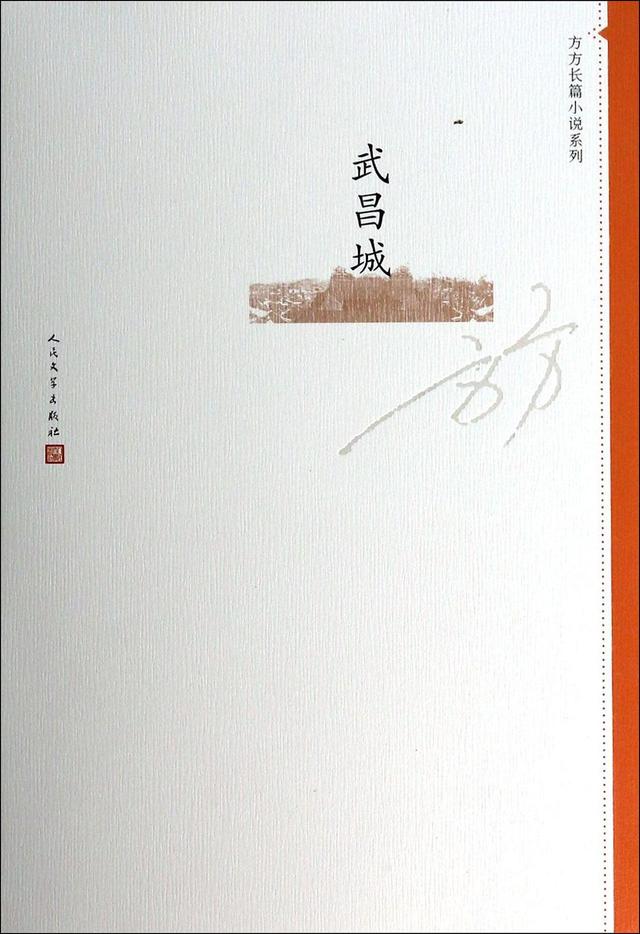
三
说实话,我的父亲非常不喜欢武汉。他对这座城市的牢骚从来不曾间断过。武汉太脏了,武汉太热了,武汉太俗了,武汉人太凶了。父亲在武汉生活了多少年,这些话就在他嘴里说过多少年。
父亲每天都骑着自行车沿着这条马路上班。他工作的机关当年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父亲是这里的工程师。这座红色的办公楼当年我们叫它“老大楼”。父亲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是在这幢楼里度过的,但他却并不快乐。政治运动的颠簸使他永远处在惶恐不安之中。 1972 年,他猝死在机关的俱乐部里,俱乐部对外又叫长江电影院。父亲为何而死我就不说了,因为说起来则又是一个国恨家仇的故事。需要说的是父亲至死都没有爱过武汉。
父亲的情绪几乎影响着我们全家。从我记事起,武汉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讨厌的地方,而南京,则是我的故乡,是永远的春花秋月。回到南京也就成为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
我为了父亲在武汉的日子写过两部小说。一部是长篇,是写父亲活着时的状态,书名叫《乌泥湖年谱》;另一部是中篇,是写父亲死时的过程,叫《祖父在父亲心中》。这座机关大院和这家电影院都在我的小说中出没,它们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消失。
四
我读书的小学在著名的二七纪念馆旁边。我在这里从幼儿园、小学一直读到初二,总共呆了九年。我们的校园很大。有好几处果园,那是我们最珍视的地方。我少年时代所有的痛苦和欢乐几乎都在这里发生。我在这里最风光的事是小学二年级我便加入了学校的火炬艺术团。我是全团最小的一个舞蹈演员。我跳舞一直跳到了初三,然后改学了扬琴。我在学校里一直是个名人。
我最初的文学创作也是由这里开始。那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写下了我人生的第一首诗。老师为此做了一次家访。她大大地表扬了我。十几年后,我终于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那就是一首诗。我总也忘不了老师对我母亲大声表扬我时的神情。
在课余时,我们经常到二七纪念馆去玩。那里的松柏郁郁葱葱,走到近处,我们就无法嬉闹。二七大罢工,是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上小学的时候,我见过许多亲自参加大罢工的人。他们对我们讲述林祥谦和施洋的故事。那些英雄的往事,曾经让我热泪盈眶。
不记得是几年级了,我和几个同学埋了一张纸条在二七纪念馆中央一个最大的柏树下,纸条上写着我们的理想,大家相约二十年后再找出这纸条,看看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没有。我不记得我在纸条上写下的是什么,我只记得少年时代的我最想当的是一名解放军记者。这个理想看来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了。
二十年早就过去了,我们没能回来找那张纸条。二七纪念馆也搬离到了别处。大柏树亦不见踪影。我就读的新村小学,后来改名叫做林祥谦学校,现在又改了回来。只是英雄们还活在我们心中。当年那些老工人讲解罢工过程的神态,在我心里依然清晰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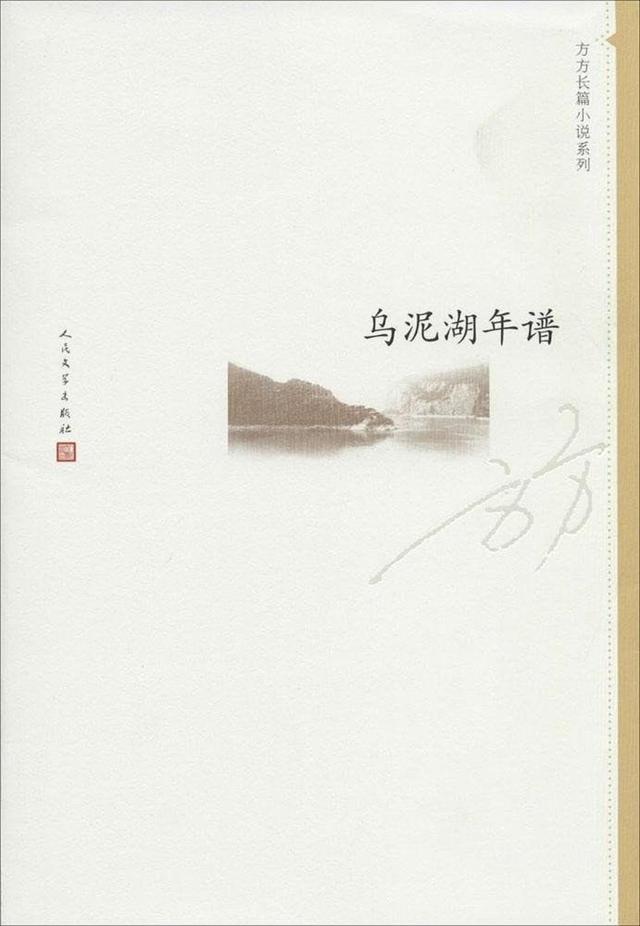
五
从我居住的地方,沿着一条路,我们可以一直走到长江边上。当年那是一条小土路,一路的沿边都青绿的菜园,菜园里有碉堡和三座坟墓。从我家出发,走路大约需要二十分钟时间就能看到长江了。
对于武汉来说,长江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长江从武汉穿心而过,它在龟山脚下挟带着汉水一起,将武汉的地面流切割成为三个大镇:汉口、武昌、汉阳。汉口在北岸,它是著名的商业大镇,大的商场都在汉口,当年武昌的人买件衣服都得搭着船到汉口来买;武昌是文化镇,几乎所有的大学都集中在武昌;汉阳则是工业镇,武汉最老的工厂都在汉阳。这样的格局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划分的。
三大镇皆临江而立,随江流而曲折。因为这个缘故,武汉人没有什么东南西北的方向感。倘若有人问路,武汉人的问答多半都是“往上走”或“往下走”。上,便是指长江上游方向,下则是指下游方向。
江水对武汉人的影响深刻到了骨髓,即便是人们随意的一指,也无不透视着水流的意味。武汉人的性格也就有点像水流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而散漫。
武汉不像北京、南京、西安那样曾为国都,因而它也从未成为过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它自古便是商业都市;可它偏偏又不像上海、广州、天津一样,它们虽然也是商业城市,可却因为临近海岸,受西方文化熏染深重。武汉地处内陆深处,洋风一路吹刮到此,已是强弩之末。所以武汉的文化带有强烈的本乡本土的味道,它和弥漫在市井的商业俗气混杂在一起,便格外给人一种土俗土俗的感觉。
但幸亏有了长江。是长江使这座城市充满了一股天然的雄浑大气。这股大气,或多或少冲淡了武汉的土俗,它甚至使得生长于此的武汉人也充满阳刚。他们豪放而直爽,说话高声武气,颇有北方人的气韵。
是长江使武汉这座城市的胸襟变得深厚和宽广,是长江给武汉的文化注入了品味,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长江,塑造了武汉人的性格。这些武汉人中,也包括我。
小的时候,我常常跟着哥哥们去长江里游泳。我的大哥和二哥把我背在背上向深水处游去,长江的水浪便从我的背上刮过,那种感觉,现在还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的游泳技能是在长江里学会的,而不是在游泳池,这使我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
我的三个哥哥都喜欢横渡长江,他们常常带着一个汽车轮胎便在江水里游来游去。从江北游到江南,曾经也是我的一个梦想,记得读高中时,学校参加市里组织的横渡长江活动,我立即报了名,可惜那一年,我们学校没有女生名额,于是,横渡长江便成了我一个永远的梦想了。
我常常想,我对长江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仿佛根本不需要说,这份热爱就一直在我心里生长。
六
其实,武汉的历史,就是人与水斗争的历史。是人进水退的历史。武汉人外战江洪,内战湖涝,经年已久。这场斗争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
与水争地,在水中筑土为墩,所以武汉遍布以墩为名的地址;
遇水架桥,水退过后,地名尚在,所以武汉也满是以桥为名的地方;
因洪筑堤,为防江洪泛滥,沿江沿河只能修堤挡水,所以武汉以堤为名的街道也比比皆是。
武汉最大的创痛也来自水。 1931 年的大水给武汉带来的灾难,足以让武汉人生生世世不敢忘记。它在一夜间令几十万人四乡流落,也在一夜间使武汉的山头变成孤岛,它使城里的屋顶有如海上浮漂的枯叶,也使市民一天死亡的人数以千计。
水落之后的武汉,面对一派颓败的废墟,挽起衣袖,重建家园。于是,几年后,武汉重新恢复了它的繁华。
说起繁华,武汉最初的繁华便是从堤上开始。
武汉最古老的街道叫长堤街。长堤街位于汉口。长堤街就像是一幅大画的轴心,武汉的城市画面从它这儿拉起,慢慢地慢慢地舒展开来。于是,它有了后来的民主路,有了江汉路,有了民众乐园,有了解放大道,有了建设大道,有了发展大道;也有了无数无数的人,在这画卷上展示自己的爱恨情仇以及生生死死。
画卷至今还在舒展,我不知道它的尽头会在哪里。只知道每一年每一年都会有新的画面出现,都会有新人诞生,旧人逝去。
这一切,都是风景。
我的小说中许多场景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在水边,许多人物也都不可避免地出没在已成闹市的堤街或没有流水的桥下。
这个都市风景给我的不只是灵感,更是创作的力量和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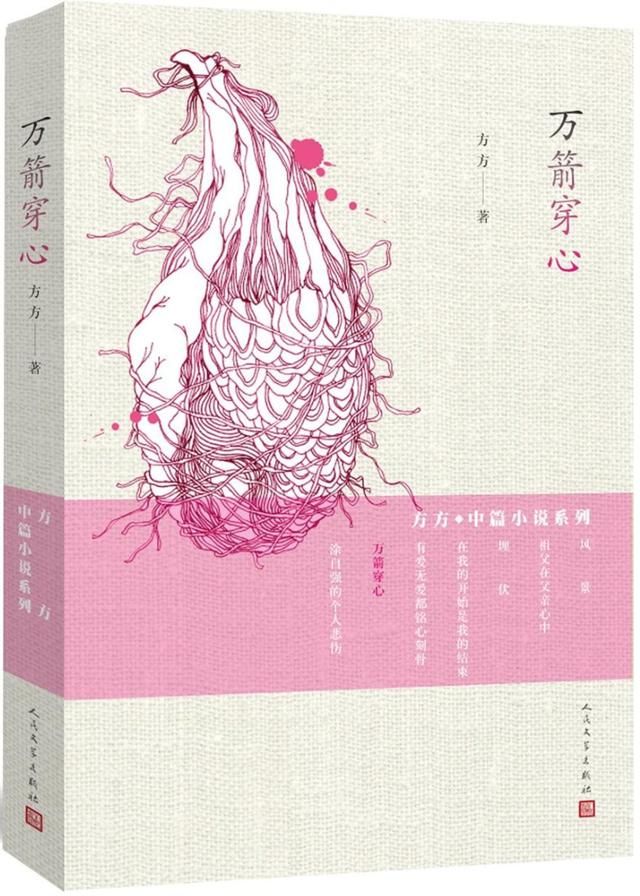
七
武汉人常说一句老话来夸耀自己。他们说:“紧走慢走,三天走不出汉口。”说的就是汉口之大。
汉口何止是大!尤其开埠以来,西方银行纷然登陆武汉,沿着江边圈起租界,盖起高楼。仿照着上海,也形成了汉口的外滩。灯火通明的街景,霓虹灯不灭的晚上,使得汉口颇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味道。繁华的概念便从这些夜夜欢场处处笙歌中透露出来。
繁华,再加上处于两江汇合口的位置,武汉表面上颇似美国的芝加哥城。所以,当年人们就管武汉叫做“东方芝加哥”。
但是武汉的闻名于世并非是因为它的繁华。而是因为枪声。
1911 年推翻清廷的第一枪不是在有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打响,也不在洋风吹彻的上海打响,甚至不是在革命领袖孙中山的老家广东打响,而是响在大陆深处的商业都市武汉。
这粒子弹一经射出,便一下子洞透了几千年的历史,让帝王时代有如多米诺骨牌,从清朝一直倒至大秦王朝。皇帝成为平民,帝王的岁月从此不在,后宫的歌声也从此失声。中国也就被这枪声引领到了一个新的纪元。
八
我一直奇怪历史怎么给了武汉这么好的机会,使它一夜成就了大名。
后来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张之洞。很久以来,我都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是十分十分渺小的。古谚云:独木难成林,滴水不成河。这都是说,人呵,你是多么的弱小。
可是有一天,我从历史书上读到了张之洞。突然间我觉得人的力量有时候是十分强大的,强大得能够塑造一座城市,能够开一代风气,能够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1889 年,张之洞以湖广总督的身份来武汉走马上任。洋务派人士张之洞有权又有见识,对于武汉来说,有这样的官员已是福气。可这个张之洞偏还喜欢有所作为。这一来,总督府所在地武汉便大得便宜了。地处内陆、经济封闭保守的武汉正是因了张之洞而开始了它生平最大的一次起飞。
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炼铁厂,为武汉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作出了最初的奠定。
张之洞在武汉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九省通衢之城。
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兵工厂,“汉阳造”曾经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武器。
张之洞在武汉大修堤防,使武汉成为今天这样的城市规模。三十四公里长的大堤至今仍屹立在这里,它的名字就叫“张公堤”。
张之洞在武汉大办教育,使得武昌的办学之风一时兴起。早期的革命者许多都是由这些学堂书院中走出,它包括著名的黄兴和宋教仁等。今天的武昌因了当年的雄厚的根基而成为大学林立之地。教育带动着科技的发达,科技则给这座城市的发展提供莫大的动力。
张之洞所做的这一切,用两个字来形容,就叫作“开放”。 虽然开放是时代进步之趋势,但在封建的帝王时代,也得要有人领先而为。张之洞就是这样一个领先的人。
有了张之洞在武汉开创的这样一个社会背景,武昌响起摧毁帝制的第一枪就不足为奇了。
可以说,张之洞当年的政绩至今仍然影响着武汉。
而时间却已经过去了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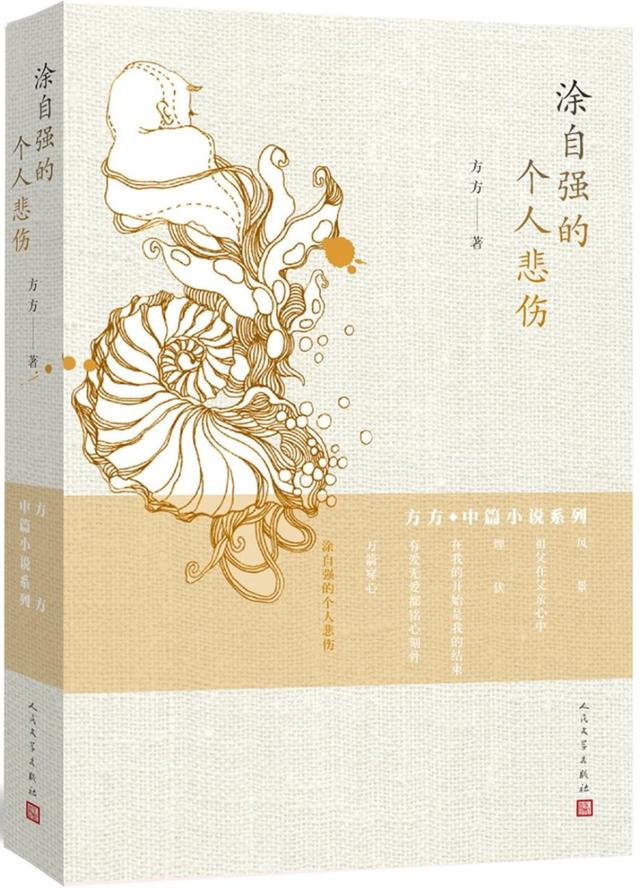
九
终于有一天,我走进了位于武昌的大学校园。
我就读的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就是张之洞在 1893 年与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一起开办的学堂之一。这是武汉的第一个专业学堂。它经过百年演变,由方言学堂,到武昌高等师范,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一直到 1928 年迁入新校址珞珈山下时,定名为武汉大学。
依山傍水的武汉大学在武汉的分量举足轻重。武汉大学是武汉的骄傲。武汉因为武汉大学的存在而陡增了几个砝码。试想,武汉若把武汉大学连枝带蔓地抽掉,武汉这座城市都会因此而失重。我曾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我对这座学校的偏爱是毫无疑问的。没有哪一所学校能超过它在我心中的分量。
大学四年的生活在我一生中至关重要。没有这四年的学习,我大概成为不了今天的我。毕业的前夕,我的一个同学对我说,大学生活对我们最重要的并不是学到了什么,而是知道了怎么去学。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同时,我还想补充一句,这便是,它使我知道了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而不是用教科书或者报纸或别人的教导。
从这座大学出来后,我便成为了一个不喜欢被人左右,而喜欢独立思考的人。
对武汉这座城市的了解,也因为上大学的缘故而得以更加深入。
因为学校在武昌,我家在汉口。为此,每星期我都在这两镇之间来来往往,从武昌到汉口,从汉口到武昌。我穿越武昌最热闹的街道,在江边最早的码头汉阳门坐船。老旧的轮船缓缓地向北岸驶去。我一次次地在江面向这被江水划开的三镇眺望,在这眺望中思索这两江于这城市的意义,也在思索中回味这个城市的一切。
后来,我在学校里写了一首诗,所有的诗句我都忘记了,只记得它的诗名叫作:《长江,我的父亲》。
十
许多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一直地在长江边上的武汉生活着。我在这里读幼儿园,读小学,读中学,在这里当过四年工人后,又在这里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仍然留在这座城市工作。掐指算来,我已经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几近四十五年了。这是多么漫长的一段岁月呵,它走得竟是那样的不知不觉。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的青春岁月差不多也就随着这江水,流走了。
有客自远方来,武汉人最喜欢带着他们四处看武汉的风景。
他们的首选当然是黄鹤楼。平民用它思乡,文人用它抒情,官人用它来显示风水。在这楼上望着浩浩江水,古人崔颢、李白、孟浩然们把诗写得美轮美奂,这当然是一个不能不来的地方。
然后他们会来琴台。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高山流水,这是何等美丽的传奇。这也是一个不能不去的地方。
然后他们还会到这碧波荡漾的东湖。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的城区中有这么大水面的湖泊,唯有武汉的东湖。东湖沿岸尽显楚文化特色,似乎是想要借风景提示人们记住我们古老的文化之源,也似乎是想要借文化来丰富湖光水色的单薄。
但我有时候更愿意带着客人在这样的街上走走。
街道在长江的两岸波浪一样展开着的。它们顺着江流的摆动而蜿蜒。所以,武汉的街道很难有一条是笔直笔直的。它们悄然地弯曲着,线条就像河流一样柔和。
街上的人们或脚步匆匆,或自在悠闲。走进这些几近百年的里巷,看着这万国旗一样飘动的衣裳,听着那浓烈硬朗的汉腔,或许会有热情的武汉人为你端一碗莲藕排骨汤,也或许会有坏脾气的武汉人对你大喝一声:搞么事沙?!
这里没有自然风光的纯净,却有人间烟火的温情。
其实,武汉人才是武汉最大的一道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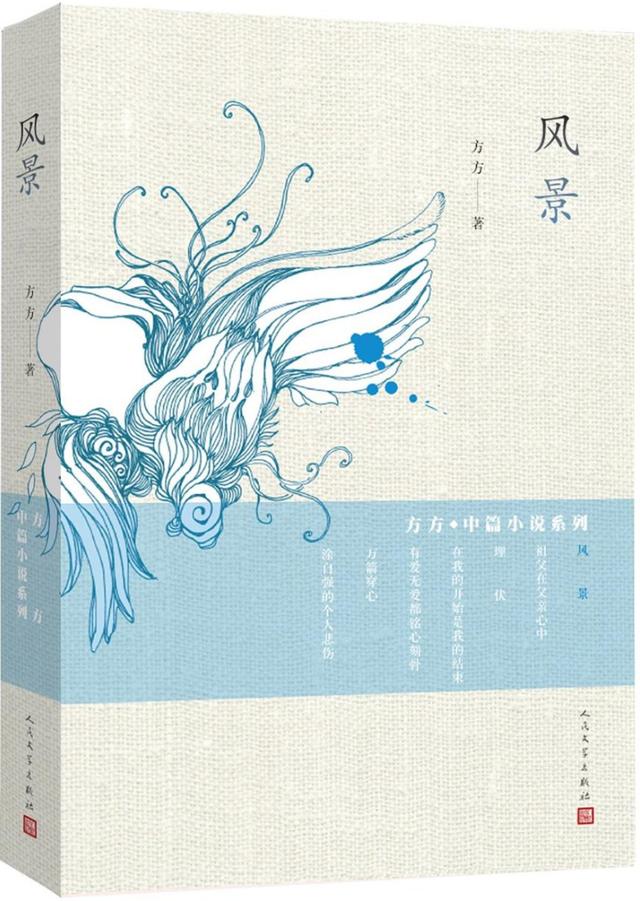
十一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经听过本土艺人敲着一节竹筒般的乐器演唱。那就是渔鼓。随着它的嘭嘭声而发出的唱腔至今仍令我觉得惊异无比。它的唱词常有几分幽默,也有几分俗气,但它的音调却含着十分的苍凉且夹杂着丝丝的幽怨。我在写小说的时候,耳边经常会想起少年时代听到过的渔鼓。有时候我想,武汉的味道,是不是就是渔鼓传达给我们的味道?
很多的时候,我都喜欢独行在这样的街上,但那悠长的渔鼓声早已消失。
我常常会想,这座城市有如一本摊开着的书,长江是它的书脊。南北两岸是它摊开的扉页。而行走的我,穿行在它的街巷中,就仿佛走在它的字里行间一样。
我曾经想要努力地去读懂它的每一行文字的内容,努力去参透沉淀在这些文字深处的寓意,努力去看清落在这些字后的阴影,努力去探知这些字后与人有关的故事。
我在这样无数次的穿行中成长。成长起来的我深深地明白:有些东西你是无法读懂无法参透无法看清也无法获悉的。你知道的永远只是表面,而隐藏在深处的东西,尤其与人的命运相关的故事,它们多半就终身地隐藏了,隐藏在历史的尘土之下,时光一层层地覆盖着它们,今生今世也无人知晓。
就说这个民众乐园吧。当年它曾经是武汉的大世界。它的这一组建筑独具一格。武汉作为大都市出现在世人的眼里,它几乎就是标志。它曾是武汉文化艺术的中心。武汉的本土文化的发展与它丝丝相连,尤其戏剧、杂技和曲艺。多少本地名角从这里走出,多少国内大腕在这里出没。这里发出的唱腔和鼓点,曾让多少武汉人欣喜若狂。而它本身在这百年历史上所上演过的一幕幕一场场也都是惊心动魄曲折回环的大戏。它几乎可以说是武汉兴衰的一个缩影。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它,只是一个充满商业气息的大杂院,商品占领了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空间,占领了本属于文化的地盘,也占领了本属于历史的地盘。它使得人们的记忆之中,除了商品,再无他物。
历史的抹去,实际上是抹去了城市自己的个性,令它像任何一个城市一样,只有一个固定的面孔。你在这张脸上,看不到“文化”这两个字。
所以,我在这样的街道上走着走着时,看着这些本可记住的历史的消失,望着它们渐渐地陈旧渐渐地颓败渐渐地毁弃又渐渐变成另一种新的模样出现,情不自禁便会有一种宿命的悲哀袭上心来。
街上永远是喧嚣的,景观亦鲜艳无比。只是,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这份喧嚣和这份鲜艳?
十三
对于武汉这座巨大的城市来说,我在1957年的加盟,只如一滴水掉入这长江中一样,可谓无足轻重;但对于我来说,它就几乎塑造了我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之成为今天的我,挖去了这座城市,我便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许久以来,我都固执地认为我是不喜欢这座城市的。我总是想要离开这里,总是觉得远方有更美好的地方在等着我。1976年唐山地震后,听说那里需要移民,我竟天真地拉着同事到处打听:我是否能移民过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我想要离开武汉的愿望十分强烈。同样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就没有走成。
但在 1986 年的冬天,我的想法改变了。
那时我业已大学毕业,分配在省电视台当了编辑。这一年的春节前夕,我被派到中央电视台学习一个月。这是我离开武汉最长的一段时间。这年的春节我在北京度过,说来也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
春节的三天,整个旅馆里寂寥无人,北方的寒风在窗外嗖嗖地吹刮着。突然间我就开始想家了,一种忧伤的情绪挥之不去。我知道这就是乡愁。
身在异乡,隔着这漫天的风雪一个人孤独地回想武汉。
这时候,我才明白,如果我有乡愁,这个乡愁的萦绕之地除了武汉,再无别处。对于我来说,它已经是一个镶嵌在我生命中的城市,它与我童年的欢乐,少年的惆怅,青年的热情,丝丝相扣;与我的梦想,我的热情,我的追求,以及我的婚姻和爱,血肉相连。我只有一脚踏在武汉的土地上,才有一种十分切实的安全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四十五年光阴的培育。与我的老家江西和我的出生地南京相比,它已经是我真正的家乡了。我想拒绝都不行,我想不喜欢它都不行。
在这个离家的冬天,我觉得我已经叛变了父亲对我的灌输。我对这个城市不再有厌恶,相反,我有的倒是由衷的喜爱。或许与其他许多城市相比,它仍然是一个有着无数毛病的地方,可是因为我在这里成长,或者说,在我成长的同时,我也看着这座城市成长。我们共同地迈着步伐,共同地改变自己,共同地走向成熟,我们知己知彼,相知已深,因此,这座城市对于我,就有了全然不同的意义。
我有时候也会问自己,跟世界上许多的城市相比,武汉并不是一个宜人之地,尤其气候令人讨厌,那么我到底会喜欢它的什么呢?是它的历史文化,还是它的风土人情?更或是它的湖光山色?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喜欢它的理由只源于我自己的熟悉。因为,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却只熟悉它。就仿佛许多的人向你走来,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张脸笑盈盈地对着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这张脸就是武汉。
所以,当我开始写小说时,这座城市就天然地成为了我的作品中的背景。闭着眼睛,我就能想象出它曾经有过的场景。它的历史沿革,它的风云岁月;它的山川地理,它的阡街陌巷;它的高山流水,它的白云黄鹤;它的风土民情,它的方言俚语;它的柴米油盐,它的杯盘碗盏;它的汉腔楚调,它的民间小曲。如此如此,想都不用去想,它们就会流淌在我的笔下。
古诗云,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武汉就是我的敬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