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
我无数次想象过大宋词人柳永的出场,但从未想过是如此的惊艳,而又如此的宿命。
这阙《望海潮》,普遍认为是柳永20岁时的作品。一个初登历史舞台的年轻人,以一支铺叙点染、自然挥洒之笔,为11世纪大宋城市的繁华日常,留下了印象派式的经典描摹。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间,这名天才横溢的词人,流荡多地,境遇窘迫,以个人的悲剧成就了11世纪最伟大的歌者。尽管那个时代的人们专注于给他打标签,认定他只是一个鄙薄、淫媟、俗艳的青楼词人,但,这只是对他的刻板偏见——事实上,他有1/4的作品在展现那个时代最有生命力的城市生活,是北宋盛世的一名忠实记录者。
人们也习惯于认定,这个“有才无行”的浪子词人,是社会秩序的局外人和破坏者,却不曾料到,一生怀才不遇的柳永都在努力向权威靠拢,争取官方与士大夫阶层的接纳,尽管这些努力均以悲情收尾。但至少可以说明,他不是主动抛弃了主流社会,而是被主流社会遗弃和伤害的人。
这阙《望海潮》的诞生,背后就是一个干谒的过程。当时,20岁的柳永从家乡福建崇安往帝都开封应试,途经杭州,拜谒世谊前辈两浙转运使孙何,这阙词类似于求见的一块敲门砖。
虽然柳永在词中仅写了杭州的城市繁华,以及投赠之人孙何虽富贵而不忘山林的书生本色,并未像唐宋时期的其他干谒之作一样阿谀媚俗,但希望借助投赠之人的影响力而让自己在科举中有所斩获的意图,仍然十分明显。
是的,天才词人柳永从一开始就是个俗人——遵从社会潜规则,渴望世俗功名,然而他的世俗和卑微,最终却无助于他被认同和接纳。而且,终其一生,直到他的晚年,他都在做这同样一件事——不停地干谒,向有权势的人投献作品,希望获得举荐。想想看,这是多么悲哀和辛酸的人生。这样一个柳永,才真正是最具悲剧性的,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唯一幸运的是,人间不过是寄身之处,在他贫病老死之后,他的作品获得了永生,迄今仍被奉为经典。

▲影视剧中的柳永形象
1
正史没有为柳永立传。没有原因,但不难想象原因——一定是修正史的宋元人,不屑于为他作传。
于是,在历史中没有传记的柳永,创造了一项历史纪录:他可能是史上在正史中无传的名气最大的人。他的名气,不仅在他死后,而是在他生前就相当大。
宋代有许多野史、笔记,都记载了柳永的逸闻。尽管这些记录真真假假,但正是这些记录,以及柳永本人的作品,才构成了后人了解这名词人的入口。
这么说吧,柳永堪称大宋第一代流行天王。
在他进入开封后,还没参加科举,就凭借音乐禀赋和文艺天才,崛起为汴京流行文化圈的领导人物。当时,“教坊乐工,每年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搞音乐的人,谱了新曲子,一定要求柳永填词,否则这曲子铁定红不了。
另一则史料记载,“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就是说,柳永靠填词,收入已经不错了,因为帝都的青楼女子都知道柳永名气大,让他有偿地给自己填个词,或在词里给自己曝曝光,分分钟就野鸡变凤凰。
柳永的词通俗易懂有风致,深得民间喜爱。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据说,邢州(今河北邢台)开元寺有个嗜酒的僧人,每次喝醉就唱柳永的词,临终前还念道:“平生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别。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明朝冯梦龙说,宋代坊间有传言:“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虽是小说家言,却大抵符合柳永生前爆红的情况。
有意思的是,柳永的词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还登堂入室,在皇宫宴会上传唱。北宋陈师道记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
“歌之再三”,有点开启循环播放模式的意思,可见宋仁宗对柳永的词是真爱。
然而,对于这样一名生活在自己治下的“人民艺术家”,作为粉丝的宋仁宗,不仅没有开启特殊照顾通道,反而成为其仕途不顺的拦路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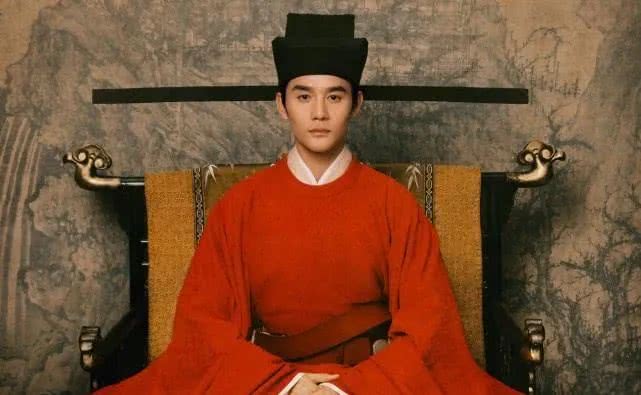
▲宋仁宗剧照
2
说起来,柳永的仕途悲剧,从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在位时就开始了。
柳永的一生,比我们想象的漫长。他大概生于雍熙元年(984年),卒于皇祐五年(1053年),历经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
他一生四五次参加科举,直到50岁时才中举。
宋真宗时期,是柳永的青壮年时期,一辈子最好的时光。但他基本上都在考场上蹉跎了,在烟柳巷挥霍了。而这两者,在他身上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在青楼冶游的文字,给他盛名,但也成为他进入仕途的屏障;而他在科举仕途上的失意,反过来使他更加纵情于青楼柳巷。
应该是在他连续科举失败后,他填了一阕词表达得不到官方认可的郁闷: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鹤冲天·黄金榜上》
这阙词细品,是八分落寞两分傲气。因为得不到官方承认,柳永才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白衣卿相”,不得不忍心割舍功名之心,偎红倚翠,浅斟低唱。这分明是一个末路途穷之人的悲歌,词人也表明自己到烟花巷陌寻访意中人,实乃是政治理想难酬的自我麻痹。
可是,在这阙词流传出去以后,来自高层的解读者却读出了满满的傲气。
在接下来的科举旅程中,柳永考中了,但仍被当朝皇帝(有说是宋真宗,有说是宋仁宗)特意将名字拿掉,并说,这不就是那个“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三变吗?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没想到柳永会以这种形式被皇帝“照顾”,以后的路只能越走越窄。怪就怪自己的词太火了,每一首都会传到最高层的耳朵里。
有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人向皇帝推荐柳永,皇帝问:“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推荐者答:“然。”皇帝说:“且去填词!”
柳永“由是不得志,日与獧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并半带调侃地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在皇帝们看来,柳永的词确实听起来很爽,但仅限于私人化的娱乐场合,而在国家治理层面,是万万不能让人怀疑帝国最高层是推崇这些淫词艳曲的,不然会引起道德人心的堕落。连带着,肯定也不能录用这个举国皆知的“淫词”作者当官,只能让他去填词,国家的道德体系才不会乱了套。
宋真宗就曾降旨说:“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糜者,皆严谴之。”阅读范围超出儒家经典,写作带有浮糜文风的人,都要严肃处理。这是朝廷要振兴儒道,纯净文化环境呀。柳永若是官场中人,肯定要被树立为反面典型进行打击。
宋仁宗在位时期,同样“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柳永的淫冶讴歌之曲,同样被当成大毒草,属于严厉打击的行列。尽管皇帝本人会以“内部批判”的名义循环播放他的曲子,但在公开场合恨不得搞一场烧毁柳永作品集的行动。

▲柳永在开封一住20年 图源/摄图网
3
问题是,整个时代写浮艳之词的人多了去了,为什么偏偏是柳永成为被打击的出头鸟?
词这种形式,是供教坊乐工、青楼女子歌唱的,从一诞生就带有俗艳俚语的特征。在苏轼特意强调词的豪放性之前,婉约词几乎一统天下,甚至连苏轼本人,绝大部分的词创作也都是婉约风。婉约,就必然多多少少带有闺门密语、浮艳虚薄,乃至淫媟鄙俗的调调。
如果硬要说创作有原罪的话,那也是词的原罪,而不是柳永的原罪。
柳永的作品集《乐章集》中,确实有不少“淫词”,赠妓、咏妓、狎妓之词比比皆是,甚至还有直接写男女交媾之词(当然,相比明清情色小说的写法还是文雅多了),被李清照批评为“词语尘下”。
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愁凝。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
洞房饮散帘帏静。拥香衾、欢心称。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摇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嘉景。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
——柳永《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
像这阙《昼夜乐》,写名妓秀香,上片写她的容貌、声音,用词已经颇为艳情,但下片更不得了,直接写男女交欢的场面,这就难怪要遭人诟病了。
因为这些“淫词”在柳永的作品集中特别扎眼,所以,尽管他还写过许多经典的羁旅词、怀古词、城市词,但通通被无视了,人们仅留给他一个标签——风流浪子词人。
然而,那个年代的大词人,无一不是这种写法。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场面怎么写得含蓄一点,所谓“雅俗之别”罢了。
和柳永同时代的张先、晏殊、欧阳修等人,都是写作男女香艳情感乃至色情风味词作的“老司机”。像欧阳修这阙《忆秦娥》:“十五六,脱罗裳,长恁黛眉蹙。红玉暖,入人怀,春困熟。展香裀,帐前明画烛。眼波长,斜浸鬓云绿。看不足。苦残宵、更漏促。”赤裸裸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柳永之词。而比柳永晚出生半个世纪以上的苏轼、秦观等人,也依然在写“笑倚人旁香喘喷”“玉纤嫩,酥胸白”等香艳词句。
但只有柳永,背负淫词之名,遭到了最猛烈的批判,付出了落榜的代价,一生仕途困顿,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为什么会这样?
其他人都以双重人格在写词,只有柳永全身心投入,不加掩饰,成为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这使得柳永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宋朝士大夫发展出文学体裁的等级论,即“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虽然都是创作,但不同体裁的创作在道德上有高低之分,文章第一,诗第二,词曲最下。张先、晏殊、欧阳修等柳永的同时代人,对这一准则的把握都很老道,戴上面具写载道文章,卸下面具写言情之词,毫不含糊。但柳永不懂这一套,别人把词当“余事”“末技”,他把词当成全部,与歌女乐工打成一片,率真而不加掩饰,难怪吃了大亏。
传统士大夫基于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认定俗艳词曲仅可以在帝国统治阶层内部把玩,因为他们读过圣贤书,有辨别力和把控力。但绝对不能在小民之间流传,否则,会导致社会道德的坍塌。带着这种道德优越感和恐惧感,他们固然会在私人场合吟唱士大夫阶层的“淫词艳曲”,但在公开场合绝对要排斥香艳绮靡之音,以维护儒家诗教的正统地位。
换句话说,士大夫有士大夫的香艳书写模式,民间有民间的香艳书写模式,二者界限分明,被认为是“雅俗之别”。柳永一定要跨界,代沉沦的青楼女子立言,这是民间的姿态,士大夫阶层是不认的。
传统士大夫阶层对文化的层级就是这么严苛,你可以说他们高傲,说他们虚伪,但就是改变不了他们的特性——他们容不下一个全身心代表民间文化的人。
据说,柳永以词触怒宋仁宗之后,曾去拜谒宰相晏殊求通融。晏殊问:“贤俊作曲子么?”柳永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冷冷地说:“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
柳永以为,同样写词的晏殊大人,一定对自己心有戚戚焉,哪知道,在晏殊大人的思想里,词与词是有天壤之别的。柳永笔下“针线闲拈伴伊坐”——歌妓一边做针线活,一边与情郎相倚相挨——这样的句子,晏殊就说自己绝对不写。
晏殊写思念,那必须是传统意境,雍容典雅,比如“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柳永那种庸俗化、日常化的场景,是他相当不屑的。所以抱歉,咱俩虽然都写词,但绝非一类人。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肯定是柳永的词更能反映时代的风貌,因为他的词是有生活气息的,带有时代的烟火气。而晏殊等士大夫的词,几乎看不到任何时代信息,有的只是传统意境的揣摩和复述,搭配私人化极强的情绪,放在唐宋元明清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成立的。也正因此,柳永的世俗化写作,在当时就打败了晏殊等人的精英化写作,不仅在民间广为传唱,还悄悄传进了皇宫。当下的真实,永远最动人。
而柳永最终被打入另册,也恰恰由于他的词太出名,无形中他被当成了市井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
枪打出头鸟,人红是非多,他被上纲上线为儒家正统文化的对立面,并作为市井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遭到正统的鄙视和唾弃,也就顺理成章了。
士大夫阶层中有真诚的个体,但作为掌控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体,则一定是虚伪的。所以他们一方面沉迷甚至模仿柳永的词风,另一方面却必须公开排斥和否定柳永的词品,进行排斥和否定柳永的人品。
整个宋代,柳永是所有著名词人中地位最低的,没有之一。

▲北宋城市繁华,在柳永词中多有体现
4
但,任何一个写词的人,都无法忽视柳永的存在。
他的词太经典了,尽管当时的士大夫对他的淫媟艳俗表示不屑,然而,背地里无不边骂边学。
宋人笔记有载,秦观和老师苏轼久别重逢,苏轼向秦观道贺说,你现在填词更厉害了,京城都在传唱你的“山抹微云”那阙词。秦观客气一番,说恩师谬奖。苏轼却接着说,但想不到我们分别后,你却开始学柳永作词了。
秦观不承认,赶紧辩解说:“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先生不要空口无凭,毁我清誉呀。苏轼则当场举例质问道:“‘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观惭愧不已。
这个故事信息量很大。秦观和苏轼的对话发生时,柳永已经故去三四十年,但他的影响力显然未减当年。从对话内容来看,被后世称为“婉约派一代词宗”的秦观,和“豪放派鼻祖”的苏轼,两人均对柳永的词作和词风相当熟稔。他们对柳永词都十分不屑,但吊诡的是,尽管他们都不愿承认,但在无形之中,却受到了柳永词深深的影响,抹都抹不掉。
苏轼调侃秦观学了柳词句法,而他自己也活在被柳永影响的焦虑里。
从苏轼的一些著名词作中,不难看到柳永的影子。比如《江城子·记梦》中的“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分明就是柳永《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转写。
而同题词作《八声甘州》,柳永对景融入人世无常的感慨,想必也给苏轼写出“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以相当的启示。因为苏轼曾称赞柳永的《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几句,“不减唐人高处”,显然是十分欣赏这阙词的。
晚天萧索,断蓬踪迹,乘兴兰棹东游。三吴风景,姑苏台榭,牢落暮霭初收。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
想当年,空运筹决战,图王取霸无休。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验前经旧史,嗟漫载、当日风流。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
——柳永《双声子·晚天萧索》
这是柳永游览苏州时写出的怀古词,沉郁苍凉,寄寓深远。大家再默念一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对比一下,是否有熟悉的味道?
柳永写“嗟漫载、当日风流”,苏轼则写“千古风流人物”;
柳永写“想当年”,苏轼则写“遥想公瑾当年”;
柳永写“江山如画,云涛烟浪”,苏轼则写“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
……
面对柳永词,苏轼的态度是矛盾的,既不屑,又赞赏,既想摆脱其影响,却又欲罢不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以自己的词终于脱离了柳永的词风而沾沾自喜,可见柳永词曾对苏轼造成多大的焦虑。
毫无疑问,柳永是苏轼在成长为伟大词人的路上,必须翻阅过去的一座高峰。这个众所周知的段子,也很能说明问题: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残风晓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苏轼当然高兴,通过豪放词的写作,他自认彻底摆脱了柳永的词风,而可以与柳永形成不同风格的双峰并峙。
同样的长路跋涉,也发生在“慢词集大成者”周邦彦身上。周邦彦的慢词声誉甚高,但明眼人都能看出,那是因为他得到了柳永的真传,所谓“周词渊源,全自柳出”。
柳永是史上第一个大量创制慢词的人,慢词因音韵和缓、篇幅较大,突破了小令的局限,从而扩大了词的内容含量。经过柳永之手,词的体式才算完备。自柳永之后,慢词成为大宋词坛主流。周邦彦正是在柳永大胆创新的基础上,受其文学恩泽,才成长起来的。
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词坛一派,但追根溯源,他们都是从柳永词分化而出。可以说,没有柳永,就没有苏轼,也没有周邦彦。宋词能发展成与唐诗媲美的文学高峰,柳永居功甚伟。
用现代文学史家郑振铎的话说,柳永的影响笼罩着整个北宋词坛。

▲柳永影响了整个北宋词坛
5
大宋词坛如此重要的一代宗师,却是体制的弃儿,这层转折发生在柳永身上,就是一幕活生生的悲剧。
你可以说他是深藏不露的扫地僧,可问题是,他本人并不愿以扫地僧的身份度过一生。
当所有人都认定他是词坛风流浪子的时候,只有他还坚信,自己要做一个温柔敦厚的儒士,寄希望并终生努力想成为一个兼济天下的士大夫。
在他40岁的时候,经历多次科举失败,他忍痛离开开封,告别心爱的情人(疑为歌妓虫娘),南下谋生,并写下了那阙最负盛名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
深藏内心的功名之念,无时不对柳永的感情造成威胁。因为执着于科举功名,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漫游之中,羁旅行役,遍及开封、江南、关中……他不停地干谒,投献奉颂之词,希望获得举荐。
终于,在他50岁的时候,命运稍微垂青于他一次。他考取了进士。
时人记载,他是在改名后才被录取的,因为“柳三变”与“淫词艳曲”构成对应关系,长期被列入黑名单,所以他才改名“柳永”。
但即便考中进士,年过半百的柳永也未迎来命运的改观。他的余生,久为小吏,在各地流走,历任睦洲推官、定海晓峰盐场盐监、泗州判官等职。他勤政爱民,政声很好,却难以升迁。最后出任太常博士、屯田员外郎等寄禄官,权小位卑,始终未能进入上层士大夫的文化圈子。
据考证,直到65岁高龄,权小位卑的柳永还在四处干谒,希望得到朝廷重用。然而,他的天才再也未能带来任何奇迹,尽管他勉力歌功颂德,但投献出去的作品大多如泥牛入海,徒留嗟叹。
柳永被嫌弃的一生,让我想起了当代王小波。王小波生前为了作品出版,为了得到承认,曾配合出版社大规模删稿、起庸俗的书名等等,但均于事无补,像极了柳永忙碌一生的干谒之旅。郁闷低落之时,王小波还考取了大货车驾照,说不行就干这个,像极了柳永曾痛苦而无奈地流连于市井圈层。
一个真实的人,游离在主流之外,寂寞孤独,他的内心总归是痛苦的。尽管事后,人们会对他们的孤独进行美化,但仍不能回避,他们是痛苦中的过来人,谁也不比谁超脱。

▲每个时代都有孤独的天才
关于柳永的最后一个悲剧传奇,源于他的死。
据说,他死时穷困潦倒,由歌妓凑钱安葬。送葬的队伍中,歌妓们缟衣素服,个个泪湿衣袖,哭声震天。她们的泪水中浸透了真诚的悲哀——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歌者,能如此为底层的女性代言;也从来没有一个老者的离去,能如此让城市的歌妓伤悲。这是对等的,也是柳永应得的。
当然,这个送葬的情节不一定真实。可以确定真实的是,活了70岁的柳永,死前肯定真切地感受到,真挚的感情不在于士大夫之间,而在于最底层的小民之间(比如他和歌妓)。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群中,他才感觉自己活过了有意义的一生。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顒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人生已然凄楚,但请相信,岁月自有公论!
谨以此文,纪念历史繁华的记录者、时代悲剧的承受者——柳永,一个在文字中活了一千年的天才词人!




